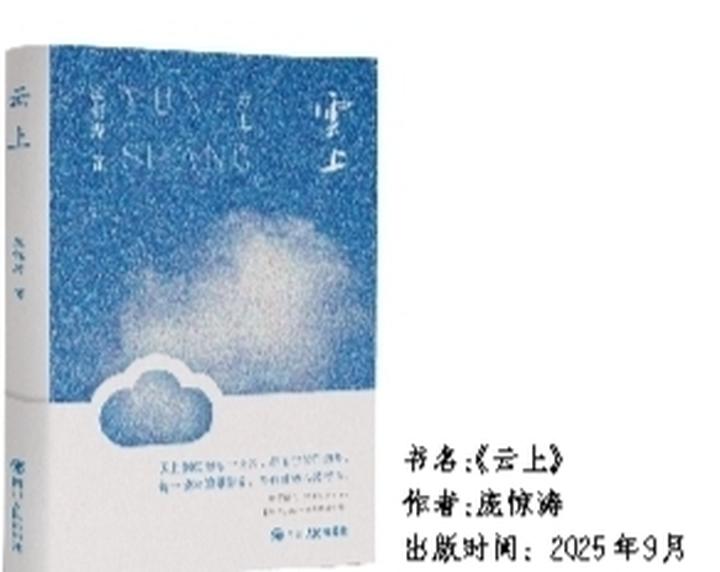
作家庞惊涛的散文集《云上》,不是悬浮于云端的浪漫想象,而是贴着大地生长的文字结晶。书中四辑“云起·故园旧事”“云驻·人间烟火”“云飞·山河远阔”“云归·浮生杂忆”,如同四片舒展的云絮,将故园、烟火、山河与自我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网,网住了那些即将被时光吹散的人间光芒——是老屋瓦缝里漏下的春光,是羌族姑娘对歌的传唱,是书院里传续的文风,更是血脉里涌动的温情。
这些光芒不耀眼,却足够绵长,在字里行间静静闪烁,照亮每个人心中与故乡、与往事、与自我对话的隐秘角落。
《云上》的开篇,庞惊涛将目光投向那座“比我还年轻”却已显衰朽的老屋。1980年建成的老屋,承载了他从童年到少年的十年朝夕,也见证了一个家庭的聚散与时代的变迁。文中对老屋的描摹细腻得令人心疼:“瓦已经稀稀落落,溃不成军,像过早谢顶的男人。”衰败的景象里藏着岁月的无情。老屋里藏着人的故事,也藏着匠人的风骨。石匠明大爷是书中令人难忘的形象——近50年的石匠生涯里,他经历过飞石袭背、锤子擦耳。凭着艺高人胆大的坚守,他将一块块顽石雕琢成“蝙蝠”“神龟”“桂树”,赋予新屋吉祥的寓意。他告诉少年庞惊涛,“采石和做其他事一样,急不得。你还得摸清石头的脾气,不能拗到上”“雕花就是逼自己做细活,也是让快的事情慢下来”。这些朴素的道理,是匠人对职业的敬畏,也是对生命的洞察。
多年后,当庞惊涛在成都买房,明大爷特意为他雕了“花开富贵”的装饰画,范公公则为他烧制了汉代瓦当摆件——老匠人的手艺与心意,成了连接故园与新居的纽带,也让故园的光芒跨越时空,照进城市的生活。
故园的记忆里,还有“十四夜”的蛴蟆灯、外婆背来的柴米油盐、夏夜晒坝的鼾声与闲谈。这些碎片式的场景,没有宏大的叙事,满是烟火气与人情味。在他笔下,故园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可触、可感、可忆的生命现场。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印记,正是人间最珍贵的光芒。
如果说“云起”是对故园的回望,“云驻”则是对人间烟火的凝视。庞惊涛将目光从乡村转向城市与乡野交织的日常,写酱哥儿的出走、三斤胡豆的骗局、安仁的轻食、云上的白鹭,每一个故事都带着生活的粗粝与温情,在细微处藏着对生命与人性的思考。
酱哥儿是一只被收养的猫,它拒绝被圈养在“豪华别墅”,用绝食争取自由。哪怕在外遭遇同类攻击、被困地下室,它也始终执著于“天地广大,自由可贵”。庞惊涛在酱哥儿身上看到了生命本真的渴望,“富足久而思自由,自由失则思苟活”。当他最终发现酱哥儿被老外Jenny当作亡妻的猫“凯维”收养时,他选择了放手。这份成全,藏着对生命与情感的尊重,也让烟火日常有了柔软的温度。
在这些烟火故事里,庞惊涛不评判、不说教,只是以细腻的笔触记录生活的原貌。他写流浪猫的生存困境,写小贩的狡黠与善良,写食客对美食的执著,每一个人物、每一件小事,都像生活里的一束微光,汇聚起来,便是人间的璀璨。比如,在“云飞·山河远阔”中的“花夜”里,由汶川姑娘出嫁仪式的对歌巧妙展开关于水的宏大叙事——岷江离开汶川,以更壮阔激荡的气势奔向下游都江堰,藏羌文化也由此开始与成都平原文化相互融合。文中,从大禹父子到李冰,再到文翁、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政治、民生功业,山河辽阔之势,在一场温暖的“花夜”中一览无余。
“云归·浮生杂忆”是《云上》最私人的部分,也是最动人的部分。庞惊涛将笔触转向自我与家族,写作为父亲的愧疚、与父亲的“战争”、家族百年的变迁,在自我审视与家族记忆的梳理中,完成了一场精神的归途。
作为父亲,他曾因工作缺席女儿多多的成长,“父爱缺席的这一年,以后拿什么都没法补上了”;他曾因家庭变故让女儿陷入病痛,“我相信,多多这场病,多半是因我而起”。这些忏悔不是廉价的抒情,而是直面自我的勇气。当他看到女儿作文里写“游泳时站在池外守候的是爷爷”“家门口的大榕树是童年的陪伴”,他才重新理解,父爱的意义不是物质的给予,而是“只要他们需要就应该到场”的陪伴。
家族百年的记忆,是庞惊涛精神归途的另一条线索。庞惊涛在家族故事里看到了“半耕半读”的传统,也看到了生命的韧性——“一百多年的家族光影,浩浩然如画卷展开,那其中无数微小的生命闪烁,于这无穷无尽的山河岁月,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云上》以细腻的笔触、真诚的情感,让我们感觉到故园的温暖、烟火的鲜活、生命的珍贵。书中的每一朵云、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人间光芒的载体,它们在字里行间挥洒,照亮我们与故乡、与生活、与自我对话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