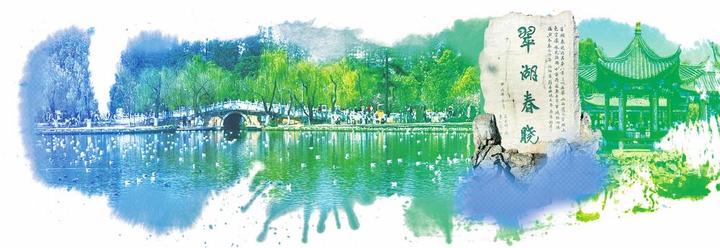
本报美编 张维麟 制图
本报记者 吴沛钊
昆明的故事,一半在滇池的浪里,一半在翠湖的波中;昆明的记忆,一半藏在“八零后”的老照片里,一半映在80后的银幕上。两代人眼中的昆明,究竟藏着怎样不同的时光印记?滇池的百年风云,又如何与翠湖边的家庭故事交织共鸣?10月12日,“两位‘80后’书写昆明故事”交流分享会在昆明璞玉书店举办,《长辈的故事》作者熊景明、《翠湖》导演卞灼,云南大学袁长庚副教授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关于家庭、城市与历史记忆的跨时空对话。
家庭叙事
连接个体与历史的时间纽带
交流的第一个主题围绕个体记忆展开。当年逾八旬的熊景明将《长辈的故事》中1909年的家族老照片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她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写家史、口述史,是把时间拖回来一点的唯一方式。”在她看来,家庭叙事绝非私人记忆的琐碎记录,而是理解社会史的“最小单元”。她提到北大历史系新生的第一份作业就是写家史,印证了“不懂家庭史,便难懂社会史”的逻辑。在她的创作中,其实并未预设中心思想或明确主题,而是通过记录十余位长辈真实而细微的经历,但这些点滴,以及百余张老照片里从长袍马褂到中山装的服饰变迁,实则正是20世纪昆明社会变迁的微观切片。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逻辑,在80后导演卞灼的《翠湖》中以影像形式延续。为了贴近“生活实感”,他刻意弱化戏剧性,模糊时代背景,原本设定在20年前的故事,因小成本无法还原旧场景而淡化时间标记,却意外让观众跳出“时代错位”的纠结,直抵家庭情感的核心。“强戏剧性让观众站在外面看,弱戏剧性才能让他们走进故事里。”卞灼解释。影片中翠湖边三代人的沉默、试探与牵挂,虽聚焦个体家庭,却折射出当代人“寻根无门”的集体困境,正如他自己年少时离开昆明后,辗转多地仍找不到“具象归处”的迷茫,恰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小家庭的缩影。
主持人袁长庚则从人类学视角明确了这种叙事的价值。他提到云南历史的“折叠性”:“看似简单的昆明家庭故事,背后藏着近代史的多重力量交织。”熊景明的家族史记录百年风云,卞灼的电影捕捉当下情感褶皱,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家庭情感地图”。在他看来,家庭叙事的本质是“对抗遗忘”,当观众从《长辈的故事》里想起外婆的口头禅,从《翠湖》中看到自家饭桌上的沉默时,个体记忆便与集体历史产生了共振。
代际冲突
不是“恶意对抗”而是“认知错位”
交流会上,“代际关系”成为最易引发共鸣的话题,而三位讲述者的共识是:当下的代际冲突,根源并非“父母不爱”或“子女不孝”,而是时代变迁中的“认知错位”与“经验鸿沟”。
熊景明以自身成长经历为参照,勾勒出传统家庭的“松弛感”。幼时父母对自己学习成绩没有过高要求,更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母亲常说‘100分能当饭吃吗?’父亲甚至曾在别人调查户口时,记错我就读的年级”。在这种“不必强求考第一”的家庭氛围中,她甚至在被父亲用勺子“吓”,敢捡勺打回去。这种“不分老幼的平等”,让她在研究三代妇女代际关系时发现“我们与母亲的关系,远好于下一代”。她将差异归因于“期待的变化”:父母那代受儒家教育却无“精英期待”,而现代父母的“爱”常与“控制”捆绑,本质是将“现代育儿理念”变成了新的“控制工具”。
卞灼的经历则暴露了现代家庭的“边界缺失”。他回忆母亲曾偷看自己日记、侵入私生活,直到现在仍试图干预他的生活。这种“以爱为名的越界”,在《翠湖》中被转化为“长辈过度关心小辈婚恋”的剧情,引发部分观众吐槽。但他并不认同“原生家庭破碎论”:“很多问题不是家庭生来破碎,而是过度关心异化成了控制。”就像影片结局“大梦一场,冲突未解决却未决裂”,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家庭状态——没有激烈和解,只有默默包容。
袁长庚则用“时代局限”为冲突提供了更宏观的解释。他举了曾在深圳任教时的例子:母亲用儿子邮箱发求助信,只因“不知道现代家庭该如何相处”。“父母那代人多来自农村大家庭,没见过‘小家庭的边界’,他们的控制不是恶意,是‘没学过更好的方式’。”他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直言:“所有人当父母时,都潜意识期待孩子复制自己的人生,但孩子本是陌生人。”这种“复制期待”与“个体独立”的矛盾,正是代际冲突的核心。
家庭未来
不拒多元,不失内核
当讨论转向“家庭文化的未来”时,三位讲述者虽视角不同,却达成了“不拒多元,不失内核”的共识:家庭形态可以变,但“情感联结”的核心不能丢。
熊景明对未来不做预判,却强调“不能把传统的好东西丢掉”。她曾在朋友家目睹孙子拒绝外婆的教育:“不要给我感恩教育”,这让她警惕“批判传统时,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在她看来,“感恩”是家庭的核心品德,“松弛”是家庭的相处智慧,无论未来家庭形式如何变,这两种内核不能失。她不反对个人主义,却希望“在个人与家庭间找平衡”,比如女儿17岁去美国后受个人主义影响,虽与她的关系难回从前,但“尊重差异”本身,就是新的家庭相处方式。
卞灼则对未来家庭充满“多元期待”。他羡慕熊景明“大家族有根”,却也接受现代小家庭的“孤岛状态”,甚至畅想100年后的家庭形态:“核心是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其实,这种期待在《翠湖》中已现端倪,影片不强调“传统家庭结构”,而是聚焦“无论如何都断不了的血缘纽带”。
袁长庚则以“包容”为未来定调。他反对“断亲”这种极端选择:“家庭里总有不可割舍的情感。”就像《翠湖》中未解决的冲突,《长辈的故事》中不同家族的差异,最终都因“包容”而共存。他从云南历史的“折叠性”延伸到家庭的“包容性”:“矛盾是随时而起随时而落的生活常态。正如昆明的天气,再热只要躲进树荫也会凉快,再冷走到太阳底下也会很快热起来。世界本身有其多样性,不必强行解决所有冲突,接纳差异就好。”他认为,未来家庭的关键,不是追求“完美形态”,而是学会“包容不同”。
从滇池风云到翠湖故事,从大家族到小家庭,两代“80后”的昆明叙事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内核: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庭形态如何演变,那份深层次的情感联系永远是我们对抗遗忘、寻找归属的“时间纽带”。而这,或许就是昆明这座城市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