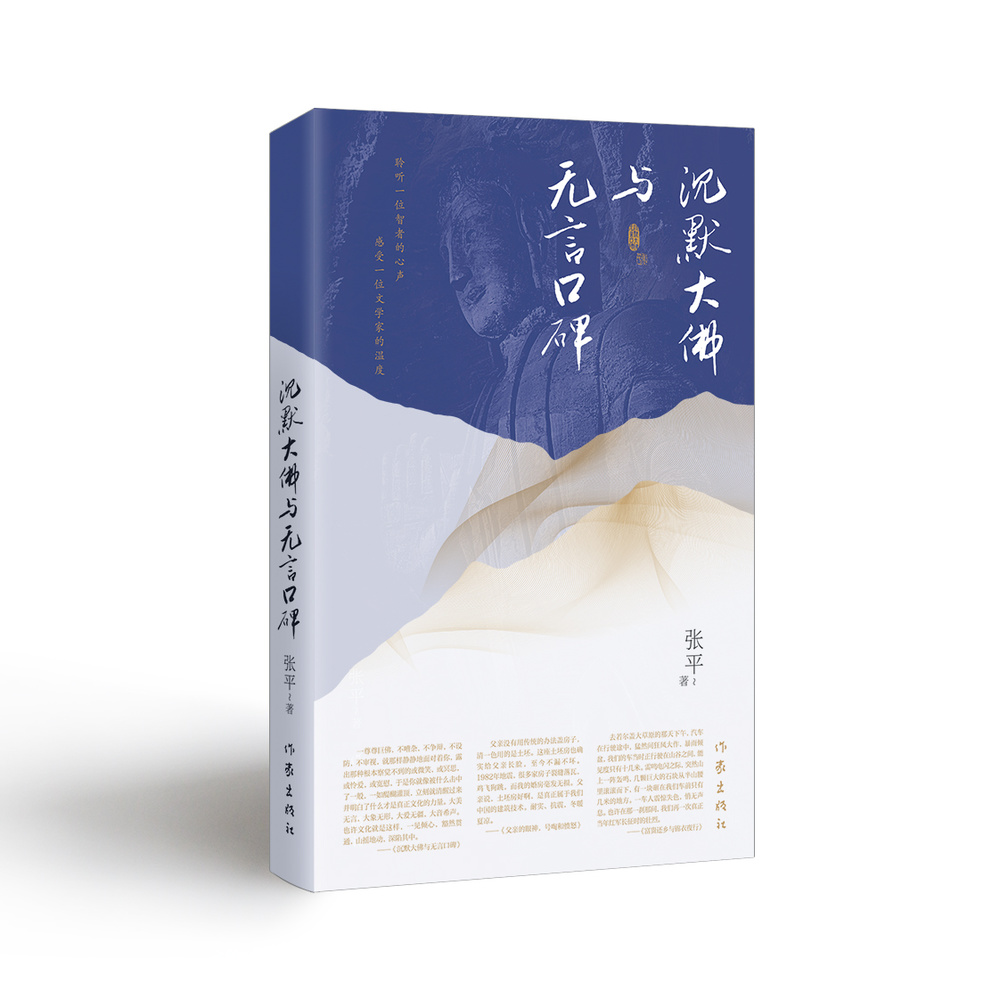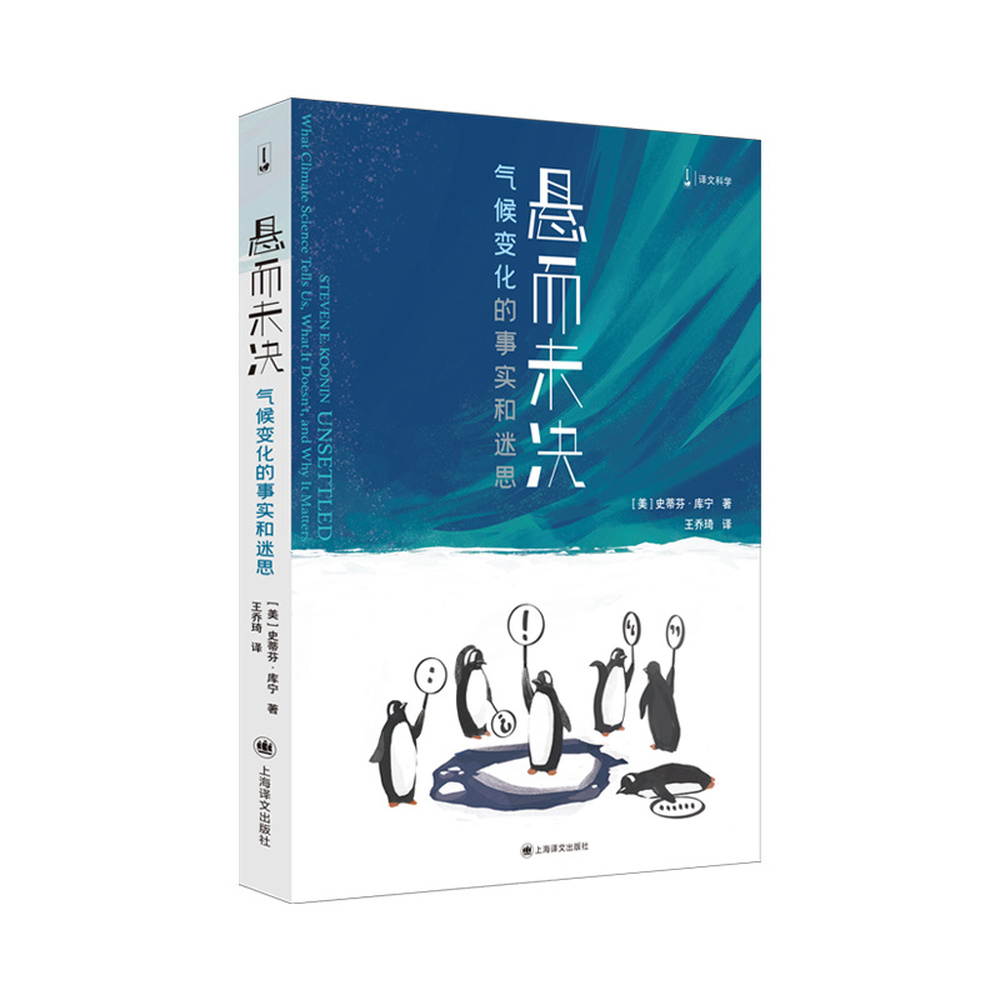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徐敏
近日,著名作家皮皮亲情散文集《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皮皮曾在20世纪90年代炙手可热,她的《所谓先生》《比如女人》《不想长大》《危险的日常生活》《全世界都8岁》等作品广受好评。这本散文集是一本写母亲、父亲、舅舅的书,更是写生与死、爱与恨的书,是她写给故去亲人和往日自己的情书,也是写给每一个正在面对衰老、面对分别的红尘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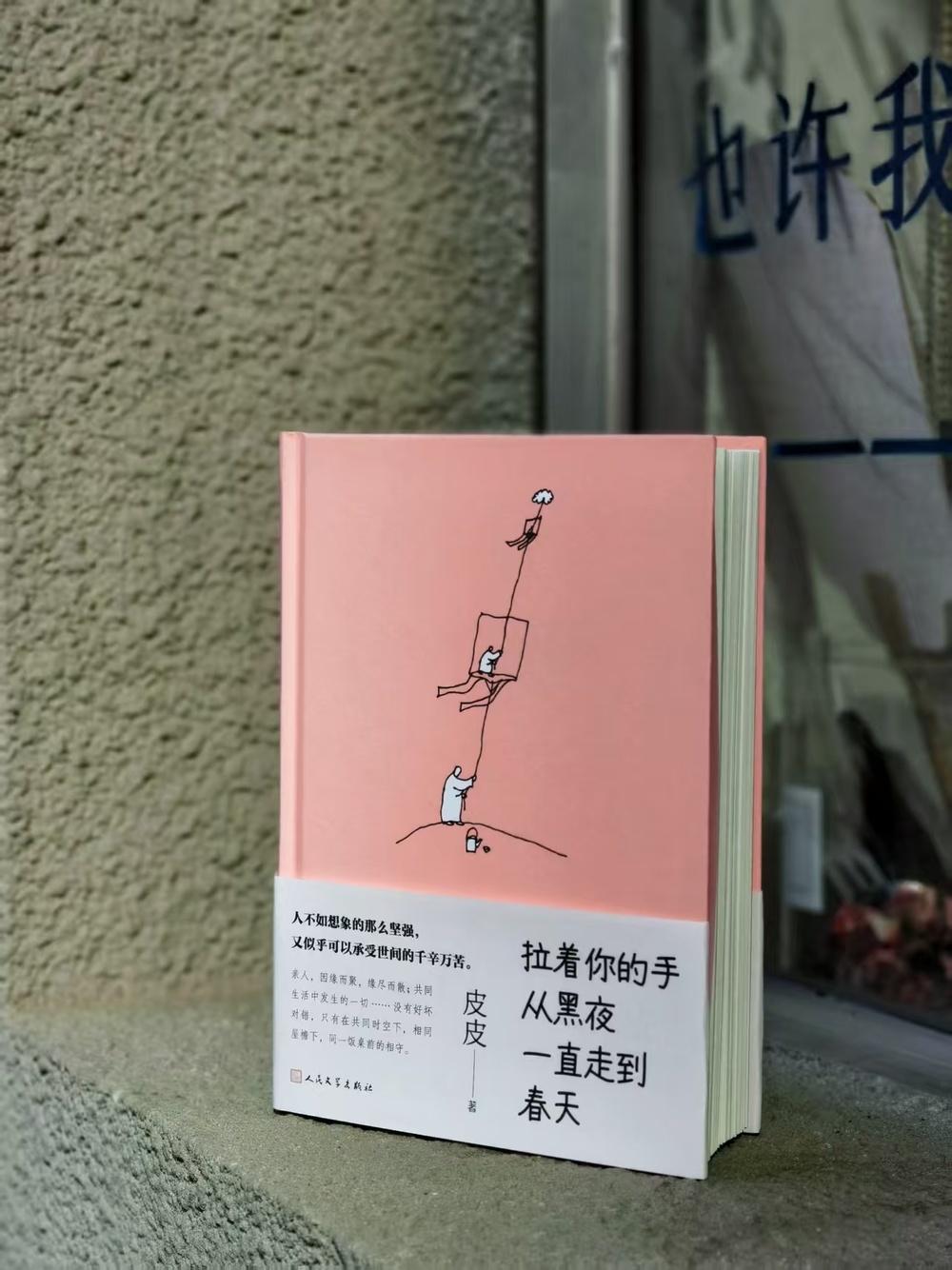
《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真实记录作家与妈妈、爸爸、舅舅告别的历程。其中有对父母冷峻的观察,对婚姻细腻的体悟,更有对父母与子女缘分一场的深刻理解和痛切反思。在真诚又略带幽默的行文中,作家力图拓展亲情散文的写作维度,不局限于对情意的讴歌和赞颂,更想把父母、舅舅作为平等的生命个体,拉开情感距离去打量、去体谅、去理解、去悲悯。作者的文字真挚动人,充满了面对自我与生命的坦诚,可谓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在书中,作者皮皮回顾了自己与父母从“对抗”走向“接纳”、从“告别”走向“重逢”的心灵旅程。在他们离开后,“我”发现自己对父母最应做到的只有一件事——陪伴。这种理解横跨生死的界河。皮皮感慨道:“他们与我的死别,发生在他们躯体死亡之前。”
在书中,作者不仅重新理解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也重新理解了父母之间的关系。皮皮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父母:母亲如花,父亲如花土,父亲的存在让母亲的生命盛放。父亲和母亲在多年婚姻中形成的关系模式,似乎是很多家庭的模式,又似乎只此一个。世上所有的婚姻或许都是如此,爱有多深,恨就有多烈。陪伴有多久,厌憎就有多长。相濡以沫和一地鸡毛,从来都相伴相生、褒贬难断。
行文至尾声处,皮皮对生与死的理解变得更加坦然。“我仍站在时间中,你走出了时间。”离去的人们只是站在了时间之外,故人们就站在金黄的麦地里,站在山与海的尽头,遥遥向我们挥手。亲人离去似寒冬凛冽,然而,春天终究会重临人间。

用书写重新还原和认识了亲情
“亲人,因缘而聚,缘尽而散;共同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我书写之时,已经变成无尽的欣慰。没有好坏对错,只有在共同时空下,相同屋檐下,同一饭桌前的相守。”
记者:这是一本回忆父亲、母亲、舅舅的书,很大篇幅涉及了疾病和死亡、分离。那书名缘何会定为《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强调“走到春天”?
皮皮: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个点,并且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可以说,“走到春天”几乎是我写这本书的核心力量。有人曾经说过照顾孩童和照顾老人的不同。照顾孩童是可以感受到成长的喜悦的;而照顾老人,尤其是照顾重病的老人,一切都指向死亡,或迟或早。这对亲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承受的。
我父母几乎是同时患病,之后在同一年内相继离世。其间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他们离世后滞留在我心里的一切,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春天”,我就无法走出来,更谈不上写什么书。
父母离世后的第五年,我逐渐意识到所经历的一切之下,还埋藏着很多我与父母,父母与我的丝丝缕缕。我开始书写时,心里几乎有一个执念:通过书写,我会发现它们。
当我完成这些文字时,发现与父母亲人之间曾经的误解和距离。看到这个层面,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所为和错误。真正面对了这些,才走出那些沉重的阴影。之后,我更真切地感到了亲人、亲情的温暖和力量。
虽然亲人已经离世,但这亲情的还原,似乎又开始了新的交往。我也对这一切有了新的理解,仿佛来到了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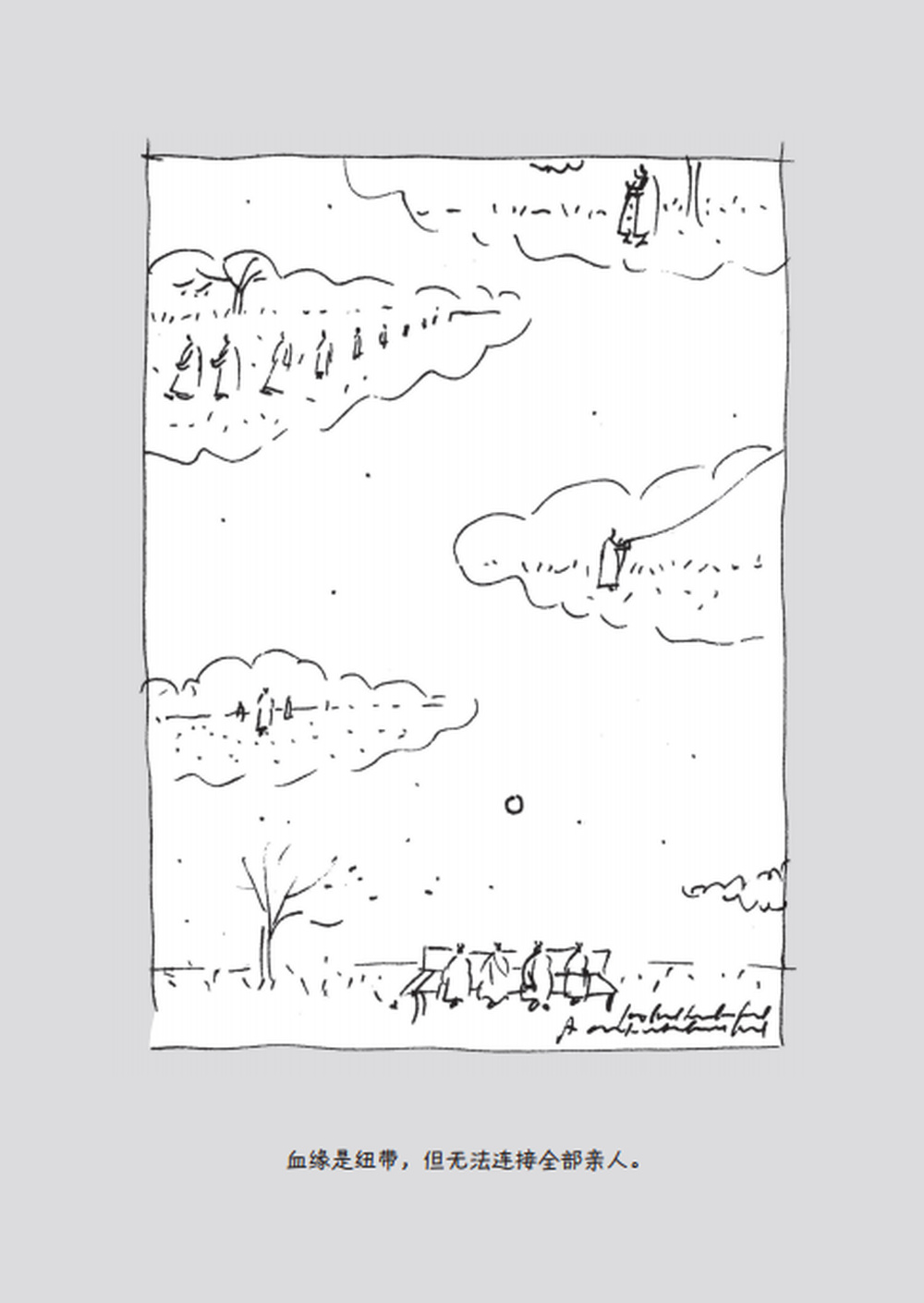
记者:比起您前期的散文作品,感觉这本《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的文字更加洗尽铅华,朴实却动人。从最初散文创作到现在,在文字风格上您有什么样的感悟和心得吗?
皮皮: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看,文字是随着心得。
随着岁月,随着时光,心开始先舍,然后才得。舍掉的那些,我感觉可以让文字更洗练,更直接,因此也更简洁。
心在舍之后的得,往往也不再是泛滥的。所以,表达上也不再铺张。

在各种关系中整理、完善、建设自己
“时光一如微风,偶尔将这次握手带回我的记忆,我最先感觉到的仍是那无力的用力,如微风吹拂落叶般平淡和随意,但它建立了我和父亲更深层面的联系。我知道了,这是父亲和我,我和父亲,似乎已经足矣。”
记者:我想,在这些文章的书写过程中,您一定重新梳理了父女、母女关系,从而对这些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否再简单谈谈您对中国的“父母与孩子”关系的理解,以给年轻人更多的感悟和思考。
皮皮:通过书写我梳理了自己与父母的交往,留下很多遗憾。
中国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有着很强的时代特点。“50后”“60后”和如今的“80后”“90后”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60后”的孩子与父母关系,给我留下的笼统印象是——大家都回避深究。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忙于工作,几乎无暇照顾孩子,多数孩子都是野生生长,或者在集体中与别的孩子共同经历了童年。这些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以后,问题出现时,只有孩子一方呼喊彼此间的问题是不够的。比如王朔就说了很多与父母的关系,但没有来自父母的回声。
“60后”很多孩子面对衰老的父母,更多是具体生活层面的照顾,交往中的包容,创伤留给自己,无法深究。当然不是所有“60后”都是这样,即使成长经历不同,他们面对父母几乎都有一样的无奈——无法真正地互动。我与父母的所谓的深究,也只是在他们离世后完成的。
至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也许有共性:那就是大家很少先放下自己的自我再面对对方。通常是各说各的理,无法共鸣便疏离回避,用其他的交往掩盖。

记者:从书中可以获知,您的父亲母亲,包括您自己也经历了不乏各种风霜的生命历程。历尽千帆后,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人到底如何才能过好这一生?
皮皮:信命,随命,不挣命。
这就像减少帆船、飞机、汽车前行的阻力。人生不易,无论谁的人生,怎样的人生,苦难是无法回避的。接受这个前提,减少挣扎的阻力,也许可以快些脱离苦难,进入新的人生境界。
我不反对个人奋斗,但奋斗的目标不是与外界纠缠,而是整理好自己,完善自己,建设自己。这种迂回的方式给我的感觉是,比直接对抗外界的困难更有效。所谓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让自己的生活渐入佳境。
人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没有标准答案。
我刚刚在这本书中给出我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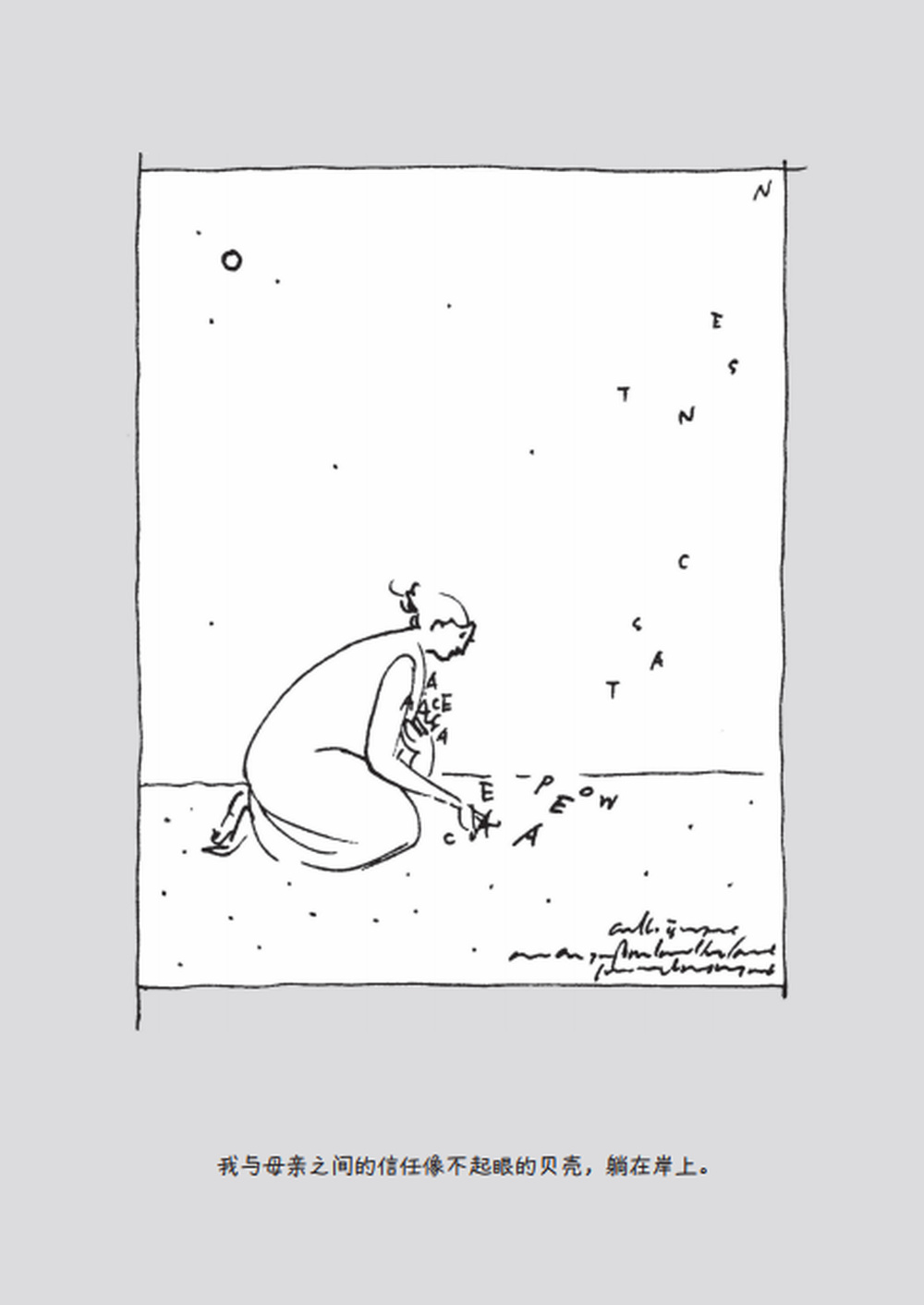
用文字治愈了人生的痛苦
“我仍站在时间中,你走出了时间。时间一点一点改变着我还有我身处的世界,面对你的青春盎然,我正无奈地衰老。”
记者:书中说,“文学疗愈过我的很多痛苦和磨难。”可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
皮皮:我写过情感三部曲,《渴望激情》《比如女人》和《爱情句号》,其中或多或少有我对情感的理解,也会掺杂很多个人经验。
我个人经历过婚姻的溃败,在痛苦中挣扎过。刚开始写作这些情感故事时,并没什么特别体会,拉开距离之后发现:在虚拟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与个人的情感经历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帮助我更好地面对个人的经历,渐渐摆脱了面对离婚常有的状态:过分在意对错、公平以及道德判断。这样的过程非常疗愈。
另一方面,从心理学层面看,在虚构故事时,作者会非常投入,处在一种忘我的状态下。某种程度上也会忘记了现实中的痛苦,这对于消磨苦难有很大的帮助。
有种电影心理疗法,心理障碍者有时难以摆脱自己的当下痛苦。进入电影院,看一部能够吸引他注意力的电影,使其完全沉浸在剧情中,就起到了疗愈的作用——他在这个电影时长里,忘记了自己,使身心得到了休息。
记者:亲情类散文是散文写作中一个很大的门类。您觉得这类散文要触达什么样的一个层次或地步,才能够真正打动读者、让读者动容?
皮皮:触自己的心;将心比心;老老实实地表达。
记者:有哪些散文作家或者文学作品对您的写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吗?
皮皮:英国作家詹姆斯·伍德的很多文章,还有王朔的散文对我的散文创作有过影响。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醒我——别装。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