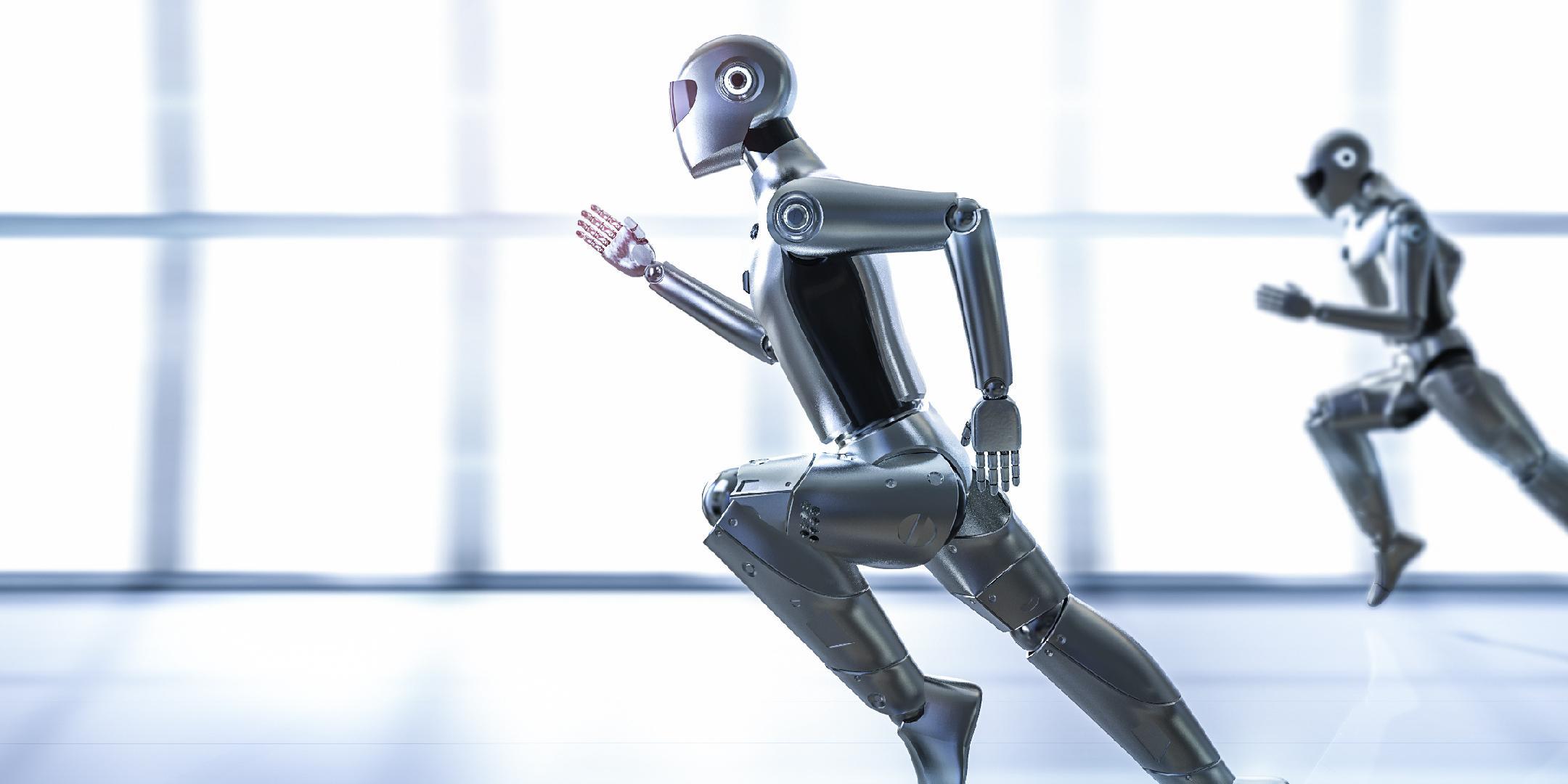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
从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剥离地方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推动市场化转型和债务风险化解”,到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要求更为严格,显示出不断增强的政策决心。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剥离”侧重于切断融资平台与政府信用的绑定,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仍允许平台以市场化主体身份存续;而“出清”则进一步要求对无法转型的“空壳类”平台进行彻底清理退出,强调“减量提质”,政策导向更具彻底性。
北方某地一位财政部门负责人认为,融资平台出清的目标虽明确,但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该负责人负责统筹当地融资平台转型工作。
该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其所在地区按债务规划融资平台退出节奏,债务越大,退出难度越高。
该负责人所在的地区去年已完成一家债务规模最小的融资平台退出工作,具体退出方式为:新成立一家国有企业,再以这家新国企的名义从银行融资,“借新还旧”。
不过该负责人说:“这种‘借新还旧’的操作存在限制,要求融资平台的债务必须是银行信贷,而不是非标融资或企业债。”
当地融资平台已经发展十余年,退出过程中需要消化大量隐性债务。去年以来的化债资金约能覆盖其中1/3,其余部分仍需地方政府自筹。目前当地政府尚未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该负责人看来,融资平台过去发展中积累的大量债务,使得地方政府在推进其退出过程中,必须筹集充足的现金流来完成债务置换,而这离不开上级部门的支持。此外,地方政府仍有大量的融资需求,因此在推动旧融资平台退出的同时,还需要同步关注新融资渠道的建立,否则融资功能可能会转嫁到其他现有地方国企或新成立的地方国企身上。
政策力度加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的经济实体。这类实体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体包括各类综合性投资公司(如建设投资公司、建设开发公司、投资开发公司等)和行业性投资公司(如交通投资公司等)。
融资平台通过举债融资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筹集资金,但随着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一些不规范行为也逐渐显现,使其成为隐性债务的主要承载主体,这些债务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全面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2014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严禁其新增政府债务。2021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快剥离地方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推动市场化转型和债务风险化解。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
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出清这一提法的变化,背后可能反映出融资平台的转型不及预期,甚至进程相对缓慢。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仍然心存幻想,认为上级政府会出手救助。
罗志恒说,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实现从“政企不分”到“市场自主”的转型。“有力”体现政策决心,这也要求地方政府加快融资平台的退出进度,各地融资平台退出时间不得晚于2027年6月末,2025年将是“平台退出大年”。
“‘有序’强调风险可控,需避免‘运动式’清退而引发新的风险,通过分类施策,实现梯度退出,防止融资平台‘一退即死’。‘有效’则聚焦‘真转型’,强调退出后的融资平台能够实现市场化运作,划清企业与政府的界限,厘清债权债务,项目建设、运营、投融资决策回归企业自主,从根本上切断对政府信用的依赖。”罗志恒称。
出清的难处
今年6月24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回顾2024年工作时披露,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融资平台数量减少7000多家。甘肃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及,2024年该省借力国家政策东风,债务风险有效缓释,高风险机构有序退出,融资平台压降94户、下降35.9%。
从地方实践来看,融资平台退出需满足明确条件。今年3月,《枝江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退出融资平台的公告》提到,根据上级关于融资平台转型退出工作的相关规定,对隐性债务已清零但经营性金融债务尚有存续,且已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完成市场化转型的平台,征得2/3金融债权人同意后,可申请退出融资平台名单。
今年6月,都昌县政府《关于报送2家企业申请退出融资平台企业名单的请示》也明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通知》要求,将都昌县两家(都昌县彭蠡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都昌县鄱湖开发有限公司)拟退出融资平台的企业清单及要件报送备案。
但在实际操作中,融资平台出清仍面临多重现实阻碍。以上述北方某地财政负责人正在处理的一个隐性债务项目退出为例:此前当地通过融资平台包装了一个项目,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融得资金上亿元。
按照项目原设计,这个项目本应有经营性收入支撑还款,但资金到账后,却被当地政府挪用于无收益的公用项目。由于项目资金用途和支出不匹配,这笔融资最终被审计部门认定为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
为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任务,上级部门要求在年底前通过专项债资金完成这一隐性债务的化债置换。该负责人说,这笔融资相比非标融资和企业债,原本有利息低、期限长的优势,但如今为了完成融资平台退出任务,不得不提前还款,反而增加了压力。
今年7月,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上半年城投行业运行回顾与下阶段展望》(下称《展望》)提到,当前城投融资政策偏严,难以真正实现化债与发展的平衡,需侧重于从保障融资循环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持续关注和回应地方合理投融资需求,优化融资政策、支持打开投资新空间。今年以来,多项融资新规有利于引导城投“真转型”,但也加大了城投可持续融资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还可能导致部分产业类国企融资难进程变慢。此外,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问题依然存在,融资渠道过度收紧易导致城投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阻碍业务发展。
《展望》进一步分析,当前“退平台”主体基本面仍偏弱、自我造血能力有待提升。在转型倒计时下,可能出现“业务拼凑”“贸易虚构”“资产转移”等新问题,需警惕“一退即死”、再次平台化等可能。现行政策要求融资平台于2027年6月前全部退出,但实际上,很多融资平台很难在这一时限内摆脱对政府项目的依赖,并具备市场化经营能力。
一位县区审计部门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由于财政收支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需求反而不断上升,这也导致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后,债务规模并未减少。
去年,他审计过的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合并方式减少了融资平台数量,但实际债务规模并没有缩减。他说:“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需求改变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地方政府借助融资平台履行经济建设职能,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而现在,对融资平台的需求则转向了补充‘三保’等刚性支出。”
一位市级财政部门负责人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清需要攻克两个难题:一是债务置换资金的来源问题,二是支出缺口的弥补问题。
在该负责人看来,针对融资平台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可能意味着财政体制管理思路正在调整——地方政府需要从以前的“借钱搞建设”的逻辑中转变过来,更加注重风险防控与效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