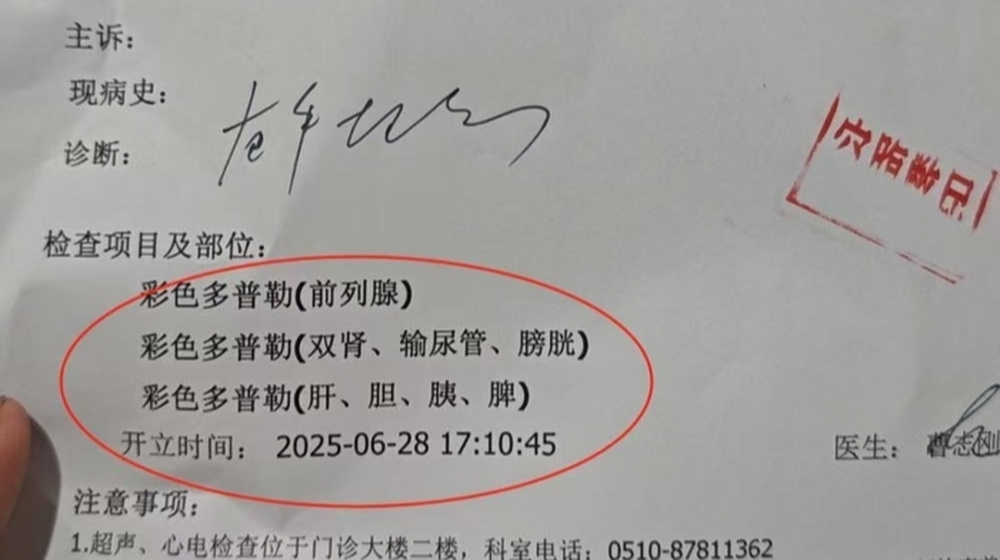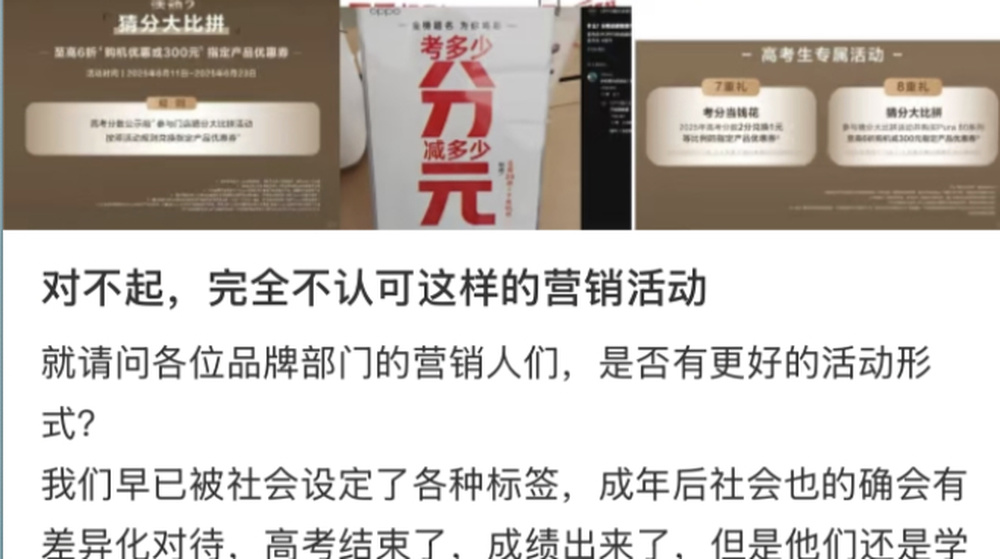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李运恒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迁徙鸟类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地处长江入海口,位于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的最东端,区域面积241.55平方公里,约占上海市湿地总面积的7.8%。崇明东滩及其附近水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敏感区,是迁徙水鸟补充能量的重要驿站和恶劣气候下的良好庇护所,是部分水鸟的重要越冬地,据调查统计,每年在保护区栖息或过境的候鸟近百万只次。同时,这里也是中华鲟及部分经济鱼类洄游的通道。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黄河记者 李运恒 摄影
伴随着保护区的持续优化提升,特别是保护区实施的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鸟越来越多了”是对崇明东滩最为直观的感受。作为众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如何最科学、最有效地管理保护区呢?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生态修复科科长冯雪松告诉新黄河记者,这是保护区近年来持续摸索的方向。他们发现,保护区内一些新命题也逐步显露,包括人鸟冲突、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等。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马志军看来,这些新命题是生态文明建设路上必然会遇到的也是必然要解决的,前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色。
长江入海口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史
“崇明东滩地处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的独特性给这里带来了典型的河口湿地、滨海滩涂湿地。”冯雪松介绍,在长江泥沙的淤积作用下,这里形成了大片淡水到微咸水的沼泽地、潮沟和潮间带滩涂。1998年,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2005年7月,崇明东滩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4年,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遗产。
上海崇明东滩的潮沟 陈婷媛 摄影
崇明东滩位于“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最南端,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中间位置,保护区内鸟类资源丰富。根据最新统计,崇明东滩已记录到的鸟类有36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东方白鹳、黑鹤、白头鹤、白尾海雕、中华秋沙鸭、黑脸琵鹭等共2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62种,如小天鹅、灰鹤、鸳鸯、小杓鹬、大滨鹬等。其中,192种列入中日候鸟保护协定,57种列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
反嘴鹬 张斌 摄影
马志军介绍,崇明东滩主要为三类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栖息地。一类是每年以鸻嘴鹬为代表的迁徙路过的鸟类,崇明东滩就是这些鸟类的迁徙驿站,鸟类在南来北往的迁徙过程中,在崇明东滩进行休息、觅食补充能量,然后为下一阶段的迁徙飞行做准备;一类是越冬的鸟类,像雁鸭类、小天鹅、白头鹤等都在崇明东滩越冬,作为这类鸟非常重要的越冬地,其主要功能是提供食物。越冬鸟主要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在崇明东滩主要取食当地一些植物的球茎或者种子等;还有一类是在崇明东滩进行繁殖的鸟类,由于近年来生态修复区的建成,很多鸟类把崇明东滩作为繁殖场所,“经过这些年的保护,包括对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治理,鸟类多样性不断提升,对鸟类的支持功能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如何最科学、最有效地管理保护区?
作为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如何能最科学、最有效地管理是保护区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课题。“湿地保护区面临着比较频繁的人类干扰,容易发生一些湿地的退化。”冯雪松介绍,外来物种的入侵治理是保护区的重点工作之一,比如上述提到的互花米草。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海漂垃圾的治理。“海漂垃圾的来源非常综合,也非常复杂,有由公海上漂过来的,有长江流域沿江的一些垃圾的积累,还有海上一些渔业生产作业等产生的垃圾,因为东滩属淤积型的滩涂湿地,所以这里成了很多海上垃圾最终搁浅的地方。”
海漂垃圾一直是保护区面临的显著且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年保护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围绕海漂垃圾开展监测活动,通过分析洋流、潮流的变化,预判垃圾分布的特点,同时也开展了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及探索了类似于“生态浮岛”等海漂垃圾再利用的路径。据了解,崇明东滩每年开展二十余场“清洁湿地”志愿者活动,此外,周边村庄居民也作为海洋垃圾巡护员,负责活动保障以及捡拾垃圾的后续预处理与清运工作,助力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开展。
海漂垃圾清理 新黄河记者 李运恒 摄影
另据了解,保护区自建立以来,不断加大野外巡护和管理力度,并通过与公安、林业等部门开展各项联合执法,及时制止偷猎偷捕等违法行为,有效地遏止了对湿地资源和自然环境的违法破坏行为。
人鸟冲突是生态保护进程必然面对的命题
近年来,崇明东滩保护区的环境持续提升,特别是对鸟类栖息地的优化,保护区内鸟类多样性大大增加,人鸟冲突的问题也逐渐被提上日程。马志军认为,“人鸟冲突的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所带来的一个新命题。”目前,在崇明东滩人鸟冲突的矛盾,主要包括雁鸭类到农田取食农作物,雀形鸟类到水果园取食,以及一些鸟类对渔业养殖的取食等。
马志军认为人鸟冲突的解决需要从多方来入手,需要多个部门、多家单位共同合作。“比如可以采取一些生态补偿的措施,由政府或者一些有责任心的企业单位等,为当地种植户、养殖户的损失提供一定的补偿。另外可以由保险公司参与,制定生态保险,从而能减少当地养殖户、种植户的部分损失。”
冯雪松也谈到,保护工作包括解决人鸟冲突等都需要联动。“首先我们跟保护区周边的农田管理单位有比较密切的交流,做一些提醒,农田如何避免对鸟类的伤害,以及怎样减少鸟类对粮食的损害等。”同时也会加强监测工作,“看看到底有多少鸟去了农田,有没有在农田发生过什么事故等等,把这些第一手资料掌握好。”
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野外监测 袁晓 摄影
此外,冯雪松还提到,未来可能通过生态保险,或者通过“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方式,“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比如说把保护鸟类所带来的这些工作成果,通过金融手段进行转化,让一些企业去购买,来补偿农民的损失等。”监测工作是为了摸清家底,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并让生态旅游跟上。冯雪松认为,保护的同时还要资源共享,让生态价值转化,让全社会能够感受到保护的价值和湿地的美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鸟类也是生态资源。”马志军提到,发掘并利用鸟类资源也是尤为关键的途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把这些保护好的鸟类的价值更多体现出来。”他解释,开展一些观鸟、生态研学等活动,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弥补鸟类对农产品或者水产品带来的损失。
马志军认为,绿色生态品牌的打造同样非常重要。崇明东滩的鸟类非常多,鸟类喜欢崇明岛这个地方,就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当地可以把鸟类做成绿色生态的品牌,利用品牌效应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来进一步补偿鸟类取食带来的经济损失。用鸟类资源来换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然后再反哺给当地。”
公民科学素质提升需要体验和教育
“体验和教育工作一定是重中之重。”在回答如何提升保护区科普宣传教育的问题时,冯雪松很笃定。他介绍,崇明东滩保护区设有专门的宣传教育部门,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投入,打造的对公众开放的科普场馆,如今每年接待人次达5万多。
上海崇明东滩科普教育基地 姚望 摄影
“我们现在的志愿者队伍是越来越庞大了,招募的讲解志愿者会定期在科普教育基地讲解或者维护秩序等,海漂垃圾的清理工作,也有相应的志愿者队伍定期来参与,身体力行为湿地保护作一些贡献。监测工作,保护区也有针对公民科学普及的调查队伍,定期参与鸟类调查工作。”冯雪松介绍。

志愿者在海滩清理海漂垃圾 新黄河记者 李运恒 摄影
据了解,崇明东滩保护区科普教育宣传方式有很多创新尝试,构建了科普教育交流合作的综合平台。先后建立了崇明东滩鸟类科普教育基地、崇明东滩湿地科研宣教中心、崇明东滩北八滧自然中心、归去来栖自然中心、社区自然教育中心,并依托上述科普场馆开展各类宣传、教育、科普及自然体验等活动,增进了社会各界对自然保护、湿地保护和迁徙物种保育的科学认识。
黑脸琵鹭 袁晓 摄影
马志军看到,当下很多公众希望能参与到鸟类保护一些活动中,特别是作为志愿者的身份。比如在崇明东滩保护区,每年都有很多向志愿者开放的活动,参与一些鸟类的调查或者鸟类环志的工作等。“鸟类是人类身边最容易看得到的一种野生动物,现在我们周边环境变好了,鸟类也多起来了。”马志军表示,从鸟类保护角度来看,普通公众首先在平时生活过程中不要干扰鸟类活动,鸟类的生存都是依赖于它所在的栖息地,保护鸟类首先要保护鸟类的栖息地,“喜欢鸟就应该远离鸟,不要靠太近。”
相关新闻>>
海漂垃圾变身生态浮岛背后:上海崇明东滩的一场鸟类保护实践样本
摄像:王春鹏 剪辑:王春鹏 编辑:刘丹 校对:李莉 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