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2023年,青年作家邵栋以其首部小说集《空气吉他》入围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这也让他和他的小说走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
“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既然已经一无所有,又何必设防?”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邵栋的全新小说集《不上锁的人》。这部小说再次入围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
《不上锁的人》中收录的七篇中短篇小说宛如七则社交网络时代的都市传奇,聚焦当代人无法摆脱的身份焦虑和边缘体验,涉及当下诸多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如身份泄露、网络犯罪、地铁偷拍、性别暴力、丧亲悼亡、异乡漂泊等等。
谁是那不上锁的人?锁住的,是谜面还是谜底?当真实与伪装交织成网,困住了每一个人,那些内心隐秘涌动的情感何以安放?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邵栋融入悬疑与推理手法,以饱满稠密的鲜活笔触,描绘当下香港社会世情百态,揭示人的情感的流变,以及人心内外的隐秘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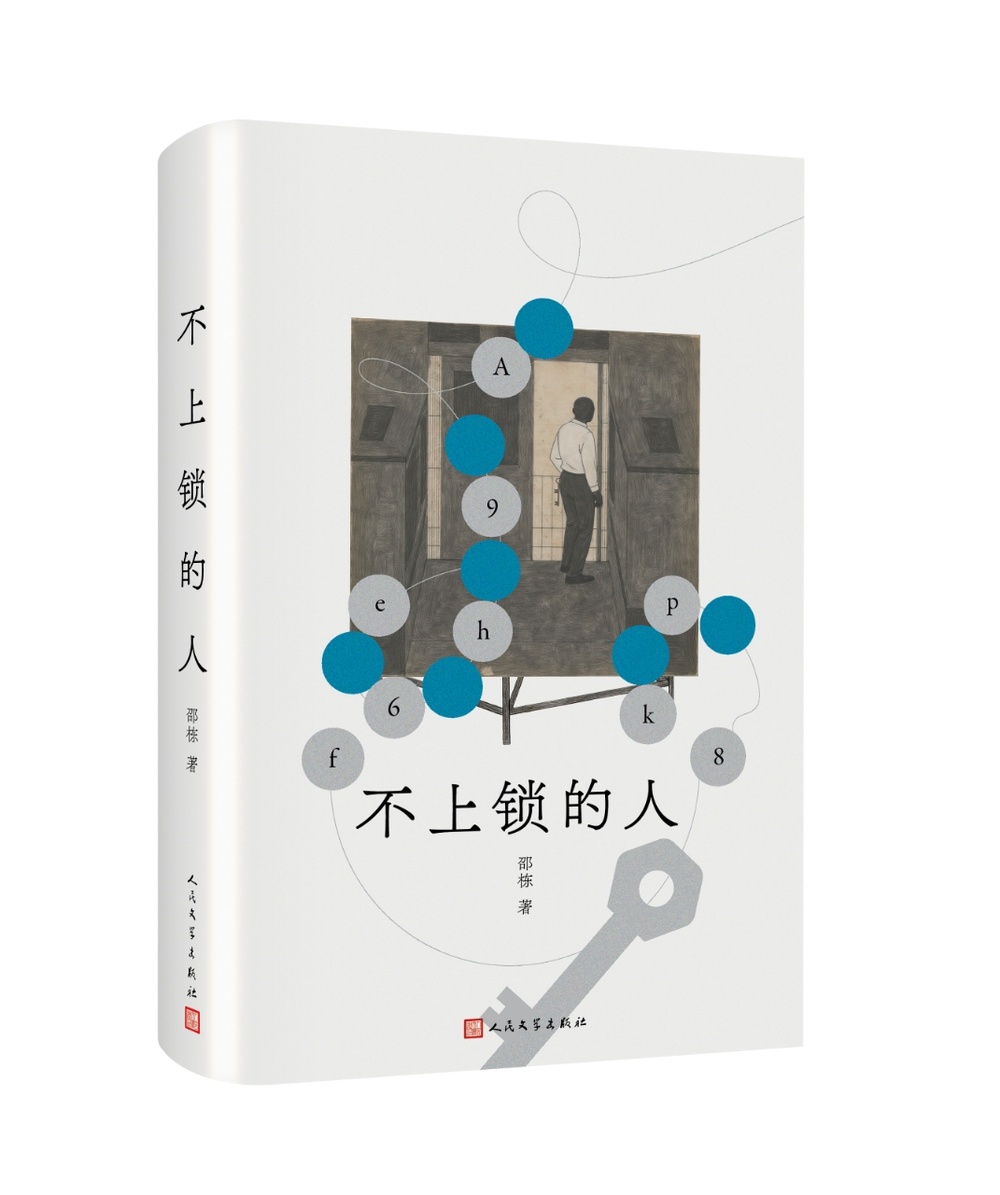
书写青年一代的普遍心理状态
记者:请简要谈一下《不上锁的人》这部小说集里的小说创作和辑录过程。在这其中,您个人最看重或者最能代表创作初衷的是哪一篇?
邵栋:过去两年多,我利用下班时间写了十几篇小说,这些小说并没有都选进来。《不上锁的人》中七篇小说的组成和排序是有一定设计的,且七篇中有六篇是中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本中篇小说集。唯一的一篇短篇是《白鲟》。
这批小说创作的起始,是在2022年阅读契诃夫的时候,我迎来了“顿悟的时刻”,突然明白自己要写作,且知道要写什么了。在这之前,我大概五年没写小说了。和上一本《空气吉他》相比,这本书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我非常清楚自己进步了很多。
其中,我最看重《文康乐舞》这一篇。一方面,《文康乐舞》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在期刊上发出来;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比较自然,同时也将设计的结构内化了。小说也有一些特殊的叙事节奏,我觉得自己处理得不错。
记者:“不上锁的人”非常精妙地定位了网络时代的很多年轻人的状态。您如何精准地选择了这种意象或者群体?“不上锁的人”更多的是指一种主动选择的开放姿态,还是一种被迫的、无所适从的脆弱?
邵栋:谢谢你对我小说的分析。其实这种状态我自己就有,而且认知逐渐深入。最开始我觉得许多人都是除了自己一副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裸命一条。后来我又想,大脑有些记忆梦想或许倒是属于自己的;再深入想一层,这些记忆,秘密和情感或许也可能被人或者网络夺去,抹杀。如此一想,自己就觉得更虚无更没有安全感了,安全感是当下一个大命题。
其实,我在书写中将自己一些上锁的情感释放了出来,在书写安全感的同时又疗愈了自己的不安。在此意义上,我觉得“不上锁的人”是青年一代普遍都有的心理状态,更多是被动的。在更巨大的东西面前,每个人都是被动的。主动只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躺平的人何尝不想昂首向前,非不愿也,乃不能耳。躺平也就是个比卑躬屈膝好一些的选择罢了。
记者:您的小说非常幽微而细致地书写了当代浮生。写作过程中,您是有意识地捕捉这些细节,还是它们自然涌现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你是如何关注和搜集这些细密的图景和信息的?
邵栋:我有个常用软件是notion,之前用过Evernote,想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和意象会随时用手机记下来,就像一个笔记本一样。小说基本上是一项骗人的本领,让人相信这件事是有可能有力量的,需要巧思。如何让人觉得真切沉浸?我觉得适当准确的细节非常重要,故事会消散,但气氛可能会一直留存。
相对来说,我是一个偏气氛的作者,所以感官细节在我的写作中比较重要。

青年作家邵栋
香港给了安静的、超越地域的写作环境
记者:《不上锁的人》这部小说集有着非常强烈的香港地域色彩,但又超越了地域,触及普遍的人性。在您看来,香港这座城市的哪些独特气质深刻地影响了您的叙事节奏和人物塑造?
邵栋:谢谢你这样说。其实我十几年前来香港读书,就是觉得这里身份混杂,不讲出身(其实后来发现也讲),始终觉得“身份归属感”这个说法相当过时。我也从来没太想着香港或者香港文学这件事,写小说是我工作之外的业余爱好,和踢足球一样。
但我素来认真,踢足球会非常认真地热身练习,穿钉鞋戴护腿板,上场也拼尽全力。写作也如此。但肯定没有做事业的心,不会觉得自己要踢职业足球,要代表香港足球出人头地;我也觉得自己和香港文学关联甚浅,肯定也总结不出什么,代表不了任何东西。譬如我没有加入过任何地方作家协会,在香港我也只加过一个五年吃一次饭的所谓的作家群,基本上属于野生作者。或许在香港,文学创作太过边缘这件事,本身就给了我的写作一种安静,可以超越地域。
记者:作为文学学者,您觉得系统的学术训练会影响具体的文学创作吗?它是否会带来一种“理论的负担”,还是说,能够提供了更理性的分析视角和更自觉的文体意识?
邵栋:学术训练会对小说写作有负面影响,因为学术太讲逻辑了。但文学是一种直接的,不须言说的直接到达,有非常暧昧灰色的地方。所以说二者是有矛盾的,因此文学批评本身是有其危险的。
但学术训练有一种特别的好处,就是会让我写作小说时的问题意识更强,对边界更自觉。有一些天赋型作家之所以后来没有更好的发展,就在于他们欠缺问题意识,只是在用本能写作自己书写了无数次的主题。
记者:您觉得,“90”后的这批作家,应该如何实践文学记录时代的功能?
邵栋:作家通常是不听建议的哈哈。关于记录时代,其实新闻、短视频、非虚构本来都有类似的功能。那虚构的文学有什么不一样,独特性何在?这是现代的作家要考虑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文学更暧昧模糊,但反而能容纳一些其他形式不许可的锐利想法与记忆,这不是文学的唯一路途,却是它的重要功能。
“青年作家很需要鼓励”
记者:古今中外,有哪些小说家或者作品,对您的写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吗?
邵栋:有个作家所有小说我都看过,他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我在技术层面学到了很多。但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万妮亚舅舅》《樱桃园》,2022年重读的时候感动不已,觉得被说中心事。他的胸襟与温柔给我特别多的触动,也让我重新燃起了写作的热情和纯粹的快乐。
记者:继《空气吉他》之后,《不上锁的人》再次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否很期待这个奖项?
邵栋:《空气吉他》报名这个奖,全是编辑老师的主意。我当时觉得报了也是白搭。编辑老师说服了我,后来幸运一路进了长名单、决名单。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可能评委看到了其中一些特别的潜质?我实在不知道。但我充满了感谢,青年作家其实很需要鼓励,我在此之前的写作历程中,尤其在内地,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鼓励。
《不上锁的人》报名前,我大概知道水准来说,应该可以入围个长名单,至少能多卖个几本书,现在入围决名单已经圆满完成任务。坦白说,入围奖项肯定是有用的,一来有奖金,二来我发现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后,虽然我还是那个我,但大家都对我客气了很多,稿件刊发也比以前快多了。总之得到的善意还是多于恶意。我还是很期待颁奖礼的,因为我去过一次,他们的招待晚宴特别好吃,气氛也特别动人,和过年似的。我见到很多业界的老师,看到他们的工作精神,自己也受鼓舞。
编辑:任晓斐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