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陈斯斯 海报设计 祝碧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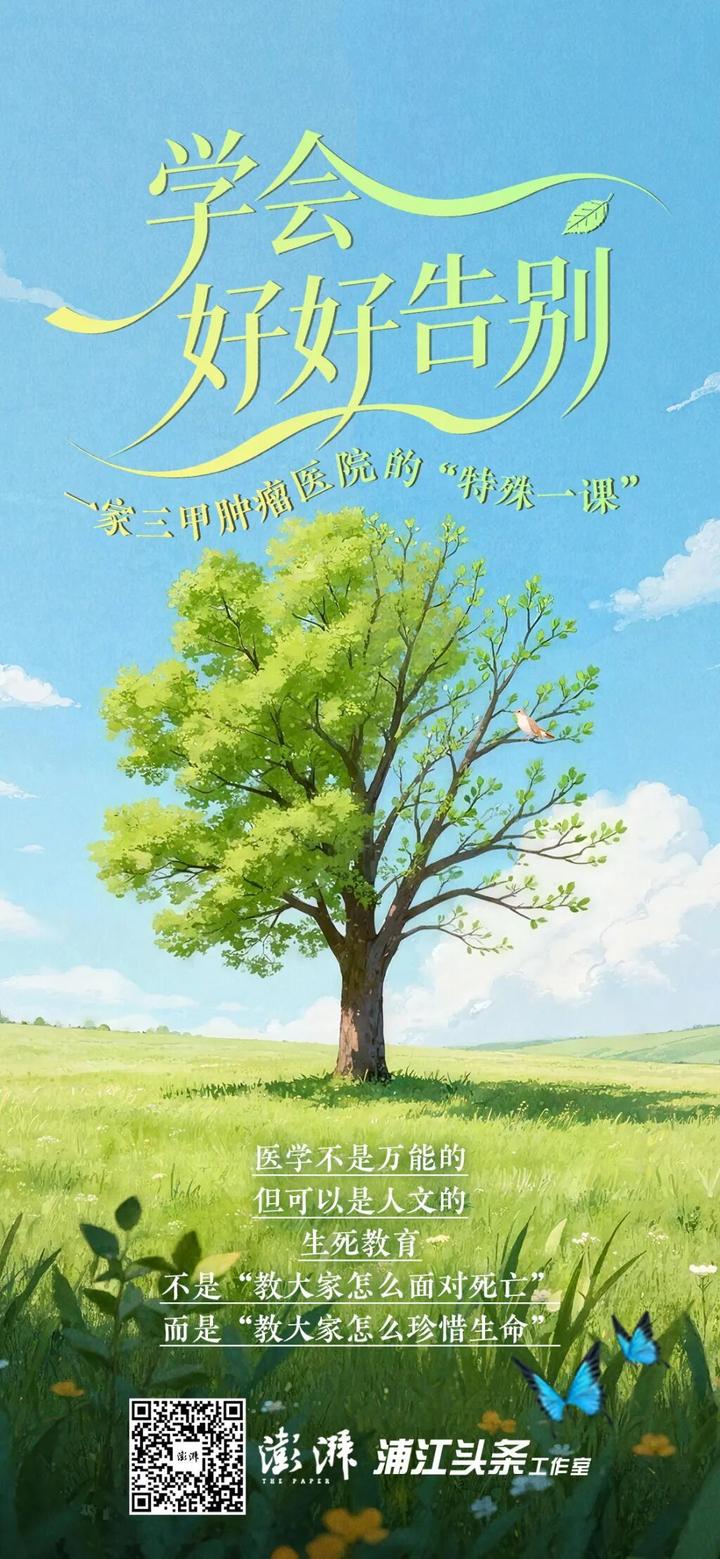
前不久,一名“90后”上海女孩与“50后”父亲对话的视频登上热搜。视频里,已确诊胰腺癌晚期且已转移的父亲,平静地向女儿传递对生命终结的看法。他劝女儿“不要为改变不了的事情悲痛”,甚至打趣说“就当我去旅行了”。
这份通透背后,不仅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宽慰,更折射出当下社会生死观念的悄然转变——越来越多人开始正视死亡,渴望有尊严地告别。
“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大众看待生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成文武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这一“特殊”科室,曾因“姑息治疗”的名字让患者望而却步,“病人以为来了我们这里就是‘放弃治疗’,但随着大众理念慢慢转变,很多晚期癌症病人主动来看我们的门诊,主动要求住院,希望自己走的时候没那么痛苦。”
“我们不以‘延长生命’为目标过度治疗,也不刻意缩短生命,仍然会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病情给患者适当加入一些抗肿瘤药物,就是让病人的身体感觉到舒服,让肿瘤在他们体内相安无事,也让病人有时间去坦然面对生命的日常。”成文武说。
作为全国三甲肿瘤专科医院中罕见的以“安宁疗护”为目标的科室,18年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累计送走1000多名患者。从2007年成立最初的6张病床,到如今经常满员的25张病床,成文武带领团队在生死交界处搭建起一座“安宁之桥”,教大家学会“好好告别”。

成文武教授坐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专家门诊。澎湃新闻记者 陈斯斯 摄
一个科室的“生死启蒙”
2005年,成文武从美国知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进修归来,带回了一个当时国内罕见的理念——姑息医学。“去之前有人跟我开玩笑,‘有本事让病人死后家属不哭,才算学好了’。”成文武起初不解,“死人怎么能不哭呢”,直到他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看到晚期癌症患者举办的一场婚礼、家属平静送别,才明白“无痛苦、有尊严”的离世,能让悲伤变得温和。
按照国内传统观念,“死亡”是一个不太愿意被提及的话题,生病了更是要全力救治。2006年,经过一年筹建,成文武开设出了“姑息治疗科”,2007年开出病房。“一开始,6张病床多是空置,‘姑息治疗’被误解为‘放弃治疗’,每次看门诊,我都要反复跟病人解释,我们不是不治疗,是不做让病人痛苦的‘无效抢救’。”成文武说。
黄喆是当时主动报名加入这一科室的护士长。“在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会遇到很多即将面临死亡的病人,如何让他们和家属平静地离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医院不仅仅是治疗患者的地方,也应该多给患者一些人文关怀。”这是黄喆当初报名的原因。她还发现,这些年也有不少护士主动报名,他们中有80后、90后,有人也经历过亲人、朋友的离世,怀着一份同理心,也善于去发现病人内心的痛苦,“我们不仅是拿技术在治疗人,而是拿真情在帮助人。”
刚开科不久,一位晚期肿瘤病人即将迎来60岁生日,成文武自掏腰包帮他买了蛋糕,医护人员围在病床前唱生日歌,还把蛋糕分给其他患者。“我以为活不到60岁,没想到还能在生前过一个这么圆满的甲子。”这位病人的话让在场家属红了眼,一周后,病人安详离世。这个场景后来成了科室的传统——为住院患者办生日会,分蛋糕、唱祝福歌,如今很多医院也有了类似的活动。
成文武还在科室走廊里腾出了一面墙,找人画上了一棵树,以“生命树”命名。“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有一棵真的树,上面挂满了患者的心愿,在我们这棵‘生命树’上,也有患者手写的一个个心愿,这是一份美好的期盼。”在成文武看来,这棵树就像“生命印记”,“让患者知道,即使走到最后,他们的心愿依然被珍视”。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病房墙上还画了一棵生命树。下图均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懿辉 摄
医学不是万能的
但可以是人文的
在这个科室,每个病床都藏着关于“选择”的故事。
黄喆至今记得,2020年遇到一位肠癌晚期多发转移的阿姨——60多岁,特别爱美,手机里存满了和姐妹出游的照片、家庭纪念日合影,即使病重,也坚持穿老年时装。当肠梗阻需要插胃肠引流管时,阿姨坚决拒绝:“我不想让小姐妹看到我插着管子的样子,宁愿开一刀,哪怕下不了手术台,也要完整地走。”
医护团队给予阿姨舒缓治疗,药物只能减轻她的痛苦,疾病进展已经无法挽回。阿姨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死后不买墓地,穿旗袍离开,骨灰撒进泥土。“家属不能理解,觉得‘不埋就是不孝’。”黄喆说,科室为此帮阿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让她当面说出心愿,“我们告诉家属,‘尊重她的选择,才是最后的孝顺’。”最终,家属点头了,阿姨穿着最喜欢的蓝色旗袍安详离世。
还有一位大学毕业刚考上公务员的年轻人,因癌症晚期接受姑息性放疗,食道黏膜损伤导致吃不下东西,情绪崩溃,说“觉得自己过不去了”。护士们得知他喜欢熊本熊,特意买了玩偶,还安排了一场“捐赠仪式”,教他用凉水减轻食道疼痛。“她后来笑着说‘没想到住院还能收到玩具’。”黄喆回忆,最终年轻人选择提前出院,在老家离世,父母在她去世后跟护士们反馈,“孩子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痛苦,感谢你们的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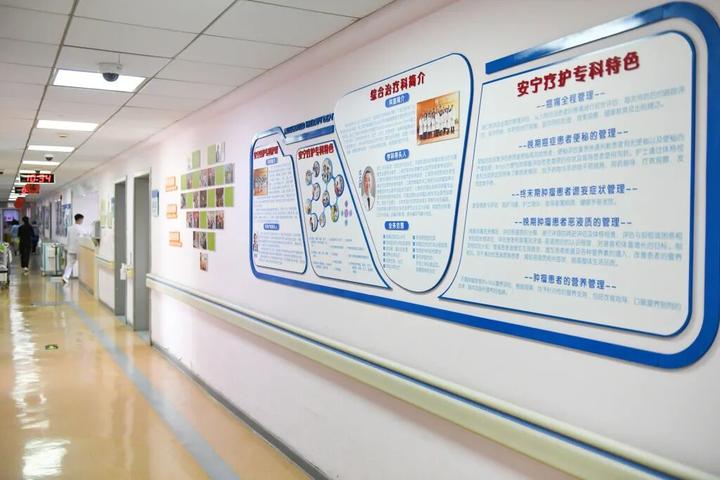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病房。
多年来,科室里也有一些转出去继续治疗的病人。
有的病人刚进来时表现出“我不惧怕死亡,后续想好了怎么样”,但随着病情和心理变化,又想要进一步治疗。家属的心情也会很纠结,不忍心看着亲人被病痛反复折磨,但情感上也有深深的不舍,希望“再抢救试一试”。成文武遇到过一位晚期癌症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呼吸困难,浑身肿胀,曾告诉医生“不想插管,想舒服点走”,家属还是坚持将他转去ICU。最终,患者还是在ICU离世。
科室里也出现过“意外的”抗癌明星。本来被预判只有几周、个把月的生存期,来这里舒缓治疗,后面活了8年、10年甚至更久的也有。但成文武坦言,“这只是个案。”
他提到一位晚期肠癌患者,15年前被断言“活不过4个月”,病人抱着“放弃”的心态送来,直言“活到哪一天是哪一天”,但经对症治疗、疼痛控制,患者活了15年,还去社区讲课分享经验,“癌症复发后,又撑了2-3年才走。”这种“超出预期”的生存期,让团队更坚信:“舒缓治疗并不是‘等死’,而是‘让活着的每一天都有质量’,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既不是加速死亡,也不刻意延缓死亡,医学不是万能的,但可以是人文的。”
让“告别”少一些遗憾
十多年来,成文武最大的感受是社会生死观念的转变,“过去跟病人谈‘生死’是天方夜谭,现在,很多晚期肿瘤患者主动来门诊,有人说‘我想舒服点,不想插管子’,有人说‘我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每天都准备好没有痛苦地走’。”
他记得科室刚开门诊时,“姑息治疗门诊”门可罗雀,有人看到名字就走,觉得“姑息”就是放弃,不看也罢。现在,门诊一号难求,全国患者慕名而来。
成文武谈到,科室从“姑息治疗科”改为“综合治疗科”是在2009年,“那时候医院取消了急诊,但仍有病人紧急就医的情况发生,医院让我们科室承担一部分接诊任务,当时就索性改为‘综合治疗科’。国内在2012年后出现的‘舒缓治疗’到后面的‘安宁疗护’理念,和最初我们的‘姑息治疗’理念是不谋而合的,都在随着时代发展变化逐步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黄喆也发现,现在的患者更愿意去表达“死亡心愿”。有患者提前写好遗嘱,告诉护士“死后想捐器官、捐角膜”,有老人跟子女约定“不抢救、不插管”,还让医生当“见证人”;甚至有患者会笑着告诉医护人员“我走的时候,要放我最喜欢的歌”。“以前家属都回避跟患者谈病情,现在会主动问‘你想怎么安排’。”黄喆说,这种坦诚,让“告别”少了很多遗憾。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文武还开设了一门“安宁关怀”课程,“患者和家属需要学会好好告别,医生更需要学会如何让患者去接受这样的理念。”他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开课,只有3个人报名,“大家觉得这个课程学了没用,但现在,限额30人的课程,总会有超额学生来主动旁听。”
在成文武看来,学会跟患者沟通“死亡”,也是医生的必修课。这门课开了7-8年,影响了几百名医学生,“未来他们走到临床,就能少一些‘无能为力’的痛苦,多一些‘理解陪伴’的温暖。”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护士长与患者交流病情,探讨患者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生死教育需要更多社会力量
事实上,对癌症晚期的治疗不仅仅是个医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成文武所说,医学只能解决疼痛,但病人离世前后需要面对的有很多,譬如病人对死亡的恐惧、病人家属的心理疏导,甚至是家庭法律财产等问题,需要更多社会资源去解决。

护士和患者一起做的泥塑。
在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病人、病人家属乃至医护人员都需要有心理上的疏导。如今,心理医生会定期到综合治疗科做团体治疗,患者和家属一起朗读、绘画、做手工和音乐疗愈等,医学院的志愿者、医务社工也会定期来与患者交流,跟着医护人员上门随访、帮助家属协调一些事务。面向医护人员开展的“死亡咖啡馆”活动从2024年起定期举办,这并不是真的聚在某家咖啡馆,而是在科室内大家聊聊工作上的患者病例,谈谈对“死亡”的理解,把这一悲伤话题变成“平常事”。
成文武愈发感受到,生死教育需要从小普及。“现在的孩子,遇到灾难、亲人离世,容易恐慌、抑郁,就是因为从来没人教他们‘怎么看待死亡’。”他进一步解释,生死教育不是“教大家怎么面对死亡”,而是“教大家怎么珍惜生命”——知道生命有限,才会更用心过好每一天;知道死亡是自然过程,才会在告别时少一些痛苦。
“就像那位在镜头上出现的女孩父亲所说的——‘一个生命要消亡,是很自然的事情’。未来,当更多人能坦然面对死亡,当安宁疗护理念走进更多社区、学校、家庭,当‘有尊严地告别’成为社会共识,或许,死亡就不再是恐惧的终点,而是‘生命圆满’的另一种开始。”成文武说。
本期资深编辑 周玉华
作者: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