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年轻时读过韩愈的《师说》。如今已年近七旬,重读这篇文章,对其中的理论新意有了更深体会:其一,从 “人非生而知之者” 出发,肯定 “学者必有师”;其二,明确 “传道、授业、解惑” 是教师的基本任务,这一表述相当精准;其三,提出 “圣人无常师”,主张广泛向他人学习,并指出 “择师” 原则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其四,认为师生关系具有相对性:“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所处的时代,教育虽已相当发达,但魏晋时期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流弊仍存。当时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既不愿求师、又 “羞于为师” 的观念盛行。韩愈写这篇文章时35岁,正在国子监任教。他借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此文,以澄清时人对 “求师” 与 “为师” 的模糊认知。
韩愈3岁丧父,由兄嫂抚育;12岁时,兄长病故,便与嫂嫂相依为命。苦难的童年,让他读书格外刻苦。然而,他的求学求官之路并不顺遂:连续四次参加进士考试才得中,随后三次应考博学宏词科均告失利。直到遇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这位伯乐,29岁的韩愈才得以步入仕途。那段屡考不中的经历刻骨铭心,也是他创作《师说》的动因之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马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古今贤文・劝学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这些话语正是他亲身体验的写照。
韩愈是有远大抱负的文人。唐德宗贞元十八年,他重新参加吏部考核并通过,次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子监是唐代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与最高学府,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共 “六学”。四门博士职位虽不高,但韩愈当时在文坛已有名望,他所倡导的 “古文运动” 正在开展,且他是这场运动公认的领袖,门下聚集了张籍、李翱、侯喜等弟子。韩愈深知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对国家前途影响深远,于是写下《请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增加国子学和四门学生员的建议;同时,他积极利用国子监这一育人场所,传道授业,奖掖后学。
随着 “韩门” 声望日增,上流社会的打压与嘲讽也接踵而至。其中最令韩愈愤怒的,是指责他 “好为人师”。与他同时期的文人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记述了他的遭遇:“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不久,这位挚爱教育的博士便在当时歪风邪气的打压下,被排挤出京,赴广东阳山担任县令。
作为 “古文运动” 的倡导者,韩愈文风 “发言直率,无所畏避”。一篇《师说》涤荡了大唐学界的积弊。韩愈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 “文”。这个 “文” 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作为 “师者”,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在延续,为后人所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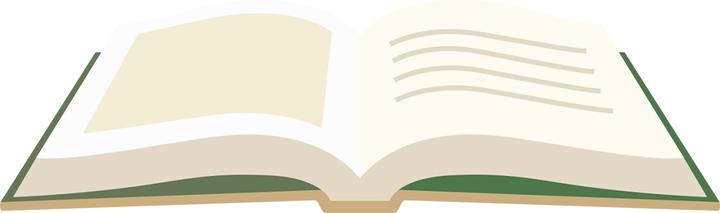
作
者
简
介
徐成文,笔名:曾闻、余力,辽宁抚顺人。在《思维与智慧》《芒种》《演讲与口才》《读者》《当代人》《散文选刊》《散文诗》《天池小小说》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2800余篇,并被多家报刊、杂志评为优秀作者。

投稿邮箱:
3822183642@qq.com
文章仅用于“云南政协报”微信公众号,无稿费。
编辑:何健美
二审:张居正
终审:张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