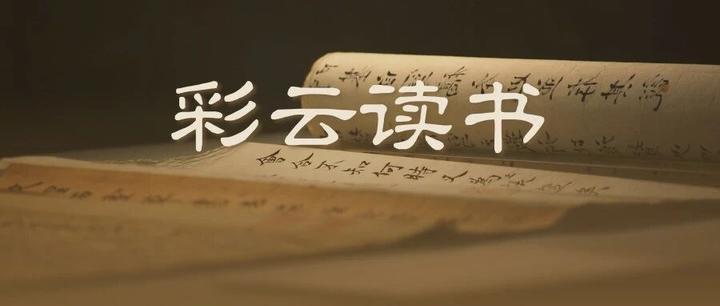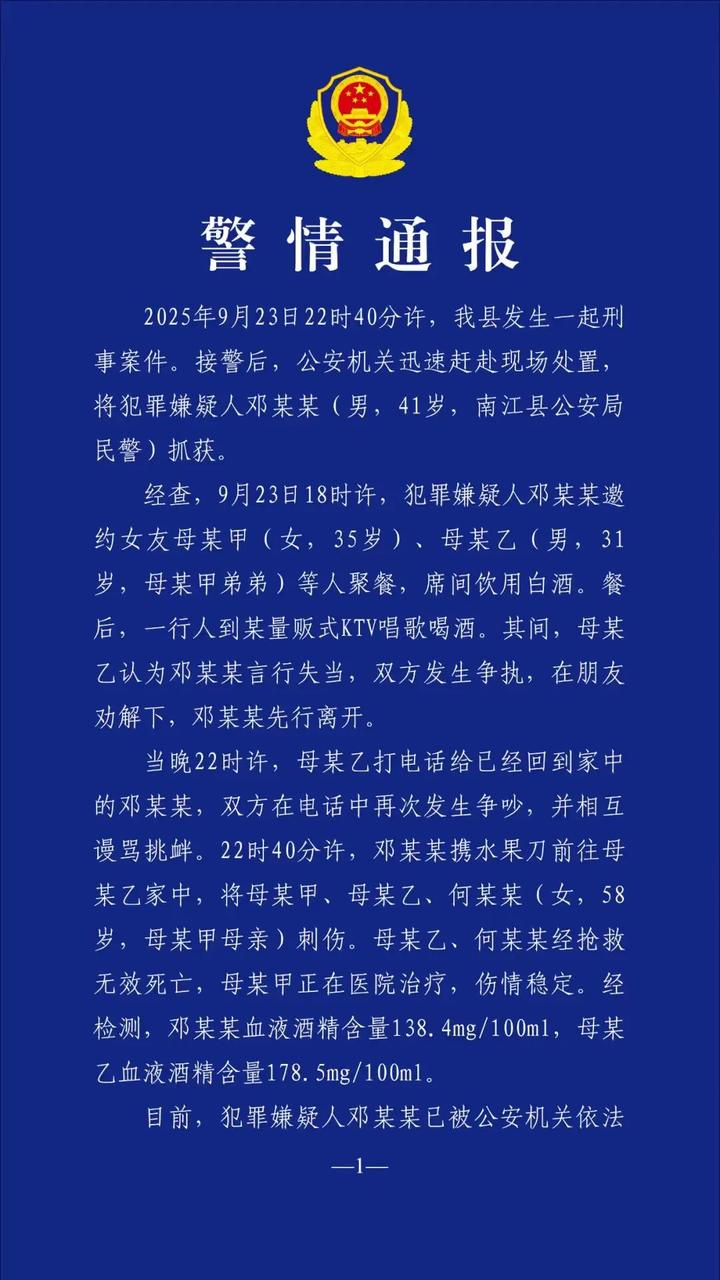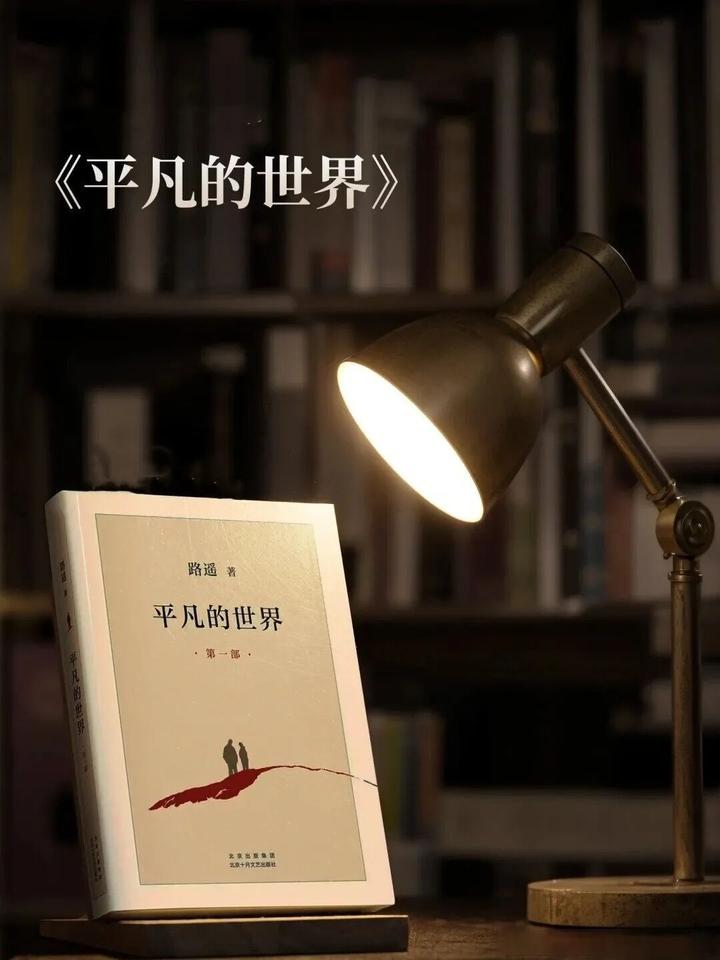
窗外秋雨绵绵,凉意透过窗棂悄悄钻进屋里。我第三次合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指尖抚过略显陈旧的书脊,竟像触到了书页里那些滚烫又厚重的日子。黄土地上的烟火起落、平凡人肩头的苦难与坚守,不再是模糊的故事,反倒像一道道清晰的纹路,在心底慢慢显影。这份因书而激起的触动,也比前两次更具体:它不再只是情绪的波澜,而是叩击出一个隐约的答案——那些我们以为普通的日常,或许正是裹着不朽力量的“生活褶皱”。我静坐窗前,任雨声与书中的人和事交织,只觉得要顺着这份厚重往下沉,才能看清褶皱里藏着的光。
我们的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恰如布满纹路与沟壑的粗布,那些藏在肌理中的印记,便是名为“平凡”的褶皱。《平凡的世界》便如一缕和煦的山风,缓缓吹开了黄土高原的沉郁,让我看见了孙少安掌心的老茧、孙少平肩头的煤屑,看到了庄稼地里的日出日落、砖窑厂的烟火明暗。这些细碎、沉重甚至带着苦涩的日常,皆是生活最真实的褶皱,却在路遥的笔下,沉淀出跨越时光的重量——那是人性里的光,是情感中的暖,是于平凡底色里静静流淌的、不朽的力量。
孙少安的人生,是被“褶皱”反复碾压又重新舒展的典型。黄土坡上的穷家、光景难挨的岁月,是他最初要扛起的生活褶皱。于是他敢闯敢拼,用一砖一瓦垒起砖厂,把汗水砸在土地里,换一家人的温饱。可命运并非坦途,砖厂倒闭的重创、秀莲病重的打击,又将这褶皱拧得更紧,勒出更深的伤痕。但他从未被压垮,在废墟上重新站起,用沉默的坚守熨烫着生活的褶皱。
而孙少平则在另一种褶皱里生长。黄原城的揽工汉生涯,是被人轻视、浸透汗水的褶皱;大牙湾煤矿的黑暗与危险,是裹挟着生死考验的褶皱。可他从未任精神沉沦,总在煤油灯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苦难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对尊严的坚守。这份在泥泞里向上生长的韧性,让平凡的生命有了不朽的锋芒。
情感的纯粹,是平凡褶皱里最温润的光,在岁月中沉淀成不朽的印记。孙少安与秀莲的爱,从一开始就扎根在黄土地的褶皱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秀莲跟着他回穷家时的笃定,是砖厂忙碌时递来的一碗热汤,是困境中那句“我陪你熬”的支撑。这份爱不掺杂质,与柴米油盐、兴衰起落紧紧缠绕,在秀莲病重时的相守里,化作了能抵御苦难的铠甲,成为少安生命里最坚实的底色。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情感,则是在精神的褶皱里悄然生长。一个是煤矿工人,一个是省城记者,身份的鸿沟本是现实的褶皱,却挡不住灵魂的共鸣。他们在黄原城的书摊上初遇,在往来的信笺里分享对世界的思考,在古塔山上定下“两年之约”。这份爱超越了世俗的衡量,带着理想主义的炽热,即便晓霞被洪水吞噬,这份纯粹的精神契合也未曾褪色,永远留在少平的记忆里,成为他在黑暗矿道中前行的光。
《平凡的世界》从不用宏大叙事注解“不朽”,而是将黄土高原上的平凡褶皱一一剖开:是少安砖窑里的烟火、少平矿灯下的书页,是秀莲递来的热汤、晓霞信里的共鸣。这些藏在日常肌理里的细碎与厚重,让我读懂不朽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而是普通人在苦难里的坚守、在泥泞中的韧性、在情感里的纯粹,是即便被生活反复碾压,也能从褶皱里舒展出来的生命力量。如今,再面对自己生活里的“褶皱”——或许是琐碎的疲惫,或许是挫折的重量,我总会想起书中那些滚烫的日子:原来认真走过的每一段平凡日常,本就藏着能穿越岁月的不朽,而这份认知,便是它留给我最珍贵的铠甲,让我能在自己的生活褶皱里,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作
者
简
介
张美存,云南省禄丰市人,高级教师,楚雄州作家协会会员。现从教于禄丰市中村乡小学,工作之余酷爱写作,习惯以细腻温润的笔触捕捉生活碎片,记录日常里的所思所感、所悟所得,字里行间满含对生活的热忱与对平凡的珍视。有数十篇作品发表于《学习强国》平台、《云南政协报》《彝族人网》《楚雄日报》《楚雄教育》等。

投稿邮箱:
3822183642@qq.com
文章仅用于“云南政协报”微信公众号,无稿费。
编辑:何健美
二审:欧阳文军
终审: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