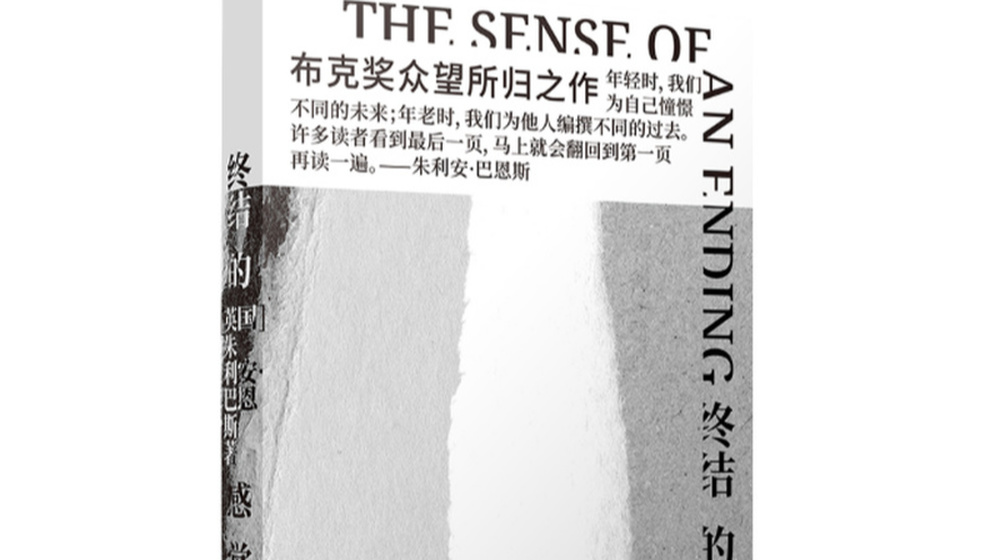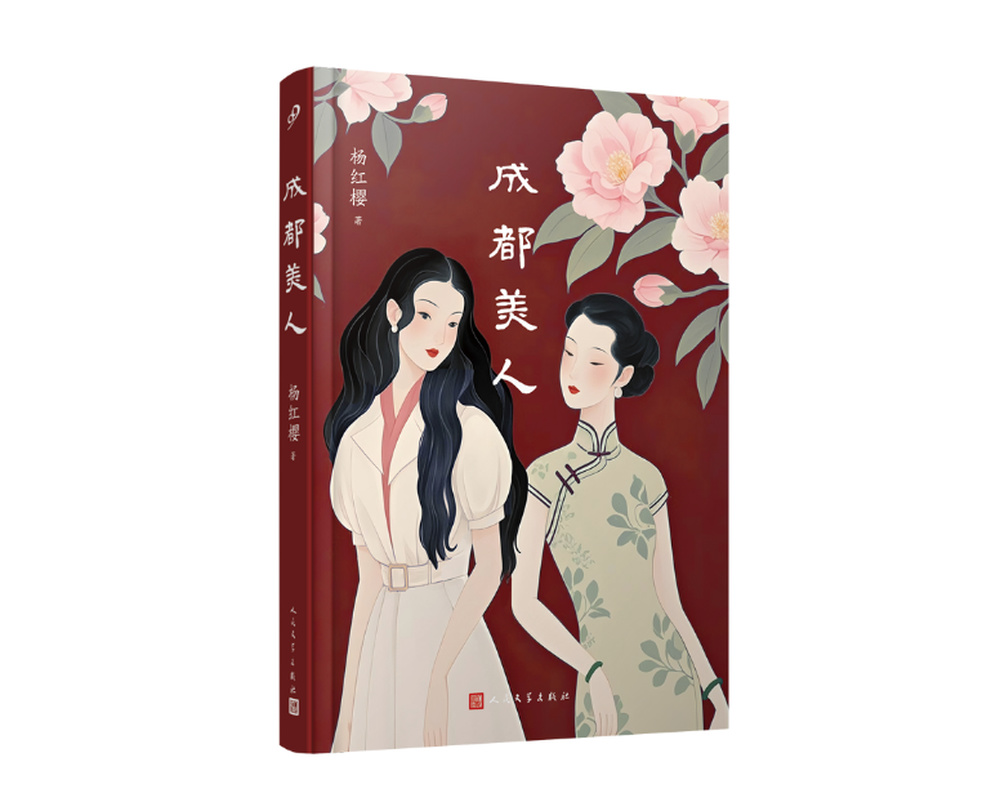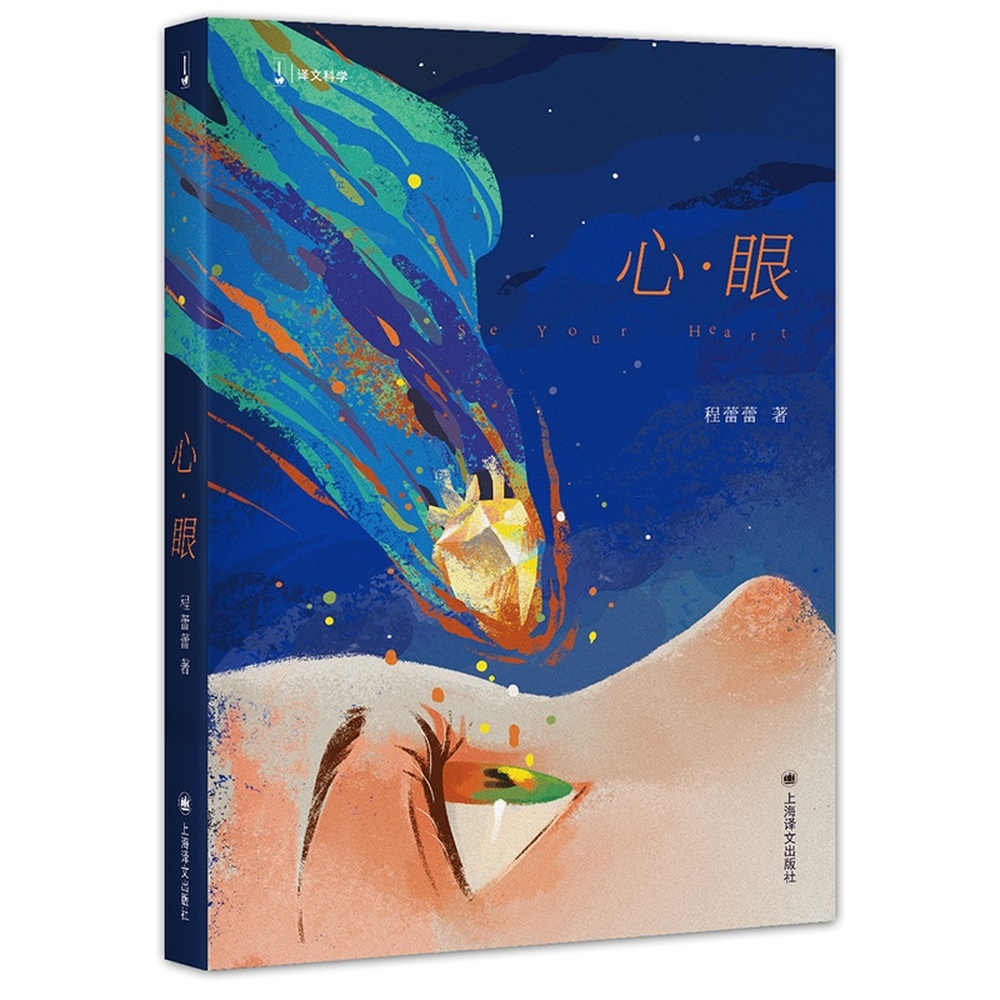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徐敏
当下,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和互联网密切相关。而互联网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流量是锦上添花还是一种枷锁?虚拟世界中的我还是我吗?人工智能和人谁更像人?这些因互联网而生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石一枫在新作《一日顶流》中给出了他的思考。
一对北京“宅男”父子,父亲胡学践是网络技术“大神”,却沉迷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儿子胡莘瓯是当下的“躺平”一族,却因为一次直播事故莫名成了顶流网红。胡莘瓯一心只想躲避众人之眼,父亲却在这时主动“暴露”,试图借儿子的流量寻找失散在虚拟世界的知己“老神”。父子俩由此闹翻,儿子负气出走躲避风头,这注定是一段“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旅途,让他体味到诸种不同的人生况味。在经历多番起伏之后,一段家庭的伤痛往事竟被揭开,而父亲沉迷网络世界、与“老神”的交往都源于此……
小说试图打通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去探求答案。虚拟世界如何成就人也摧毁人,如何一步步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甚至成为现实?石一枫借一个“社恐”顶流出逃的故事,全方位扫描互联网时代中的众生相和心理趋势,书写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评论家贺绍俊评价《一日顶流》:石一枫正是通过一个顶流的故事形象描述了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个图像时代是怎么形成的。小说演绎了一场主人公不愿成为顶流的既荒诞又现实、既好笑又辛酸的逃遁传奇,从而揭露出图像时代的资本与消费内幕。逃遁并不能解决时代的问题,石一枫让逃遁到孤岛上的主人公开启了寻觅之旅。在这条路径上,我们看到了数字化的巨大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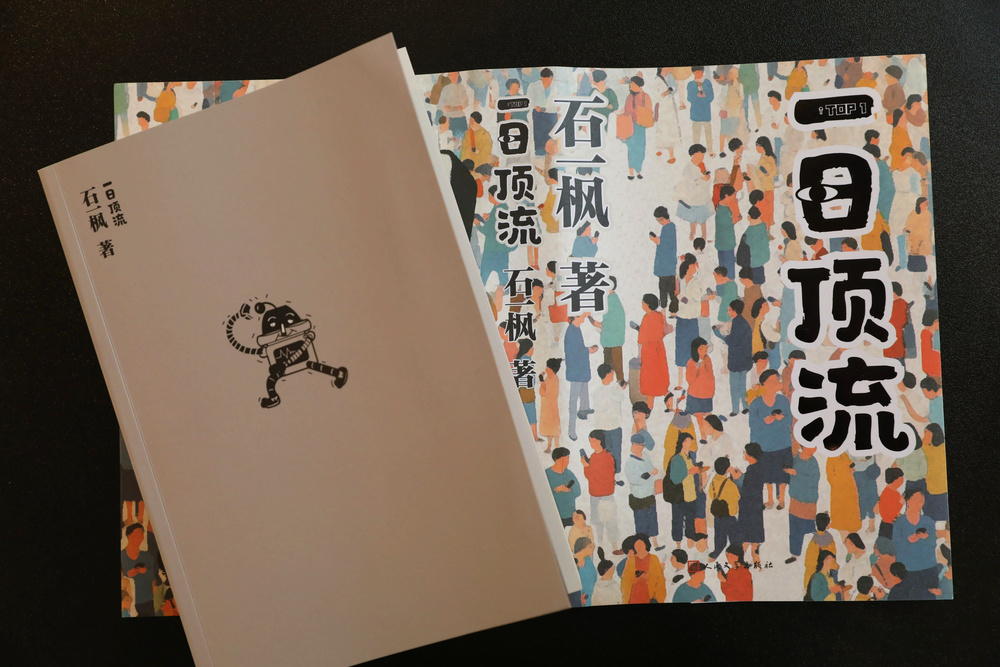
呈现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记者:“互联网生活史”是当下文学创作中一个很新的题材。《一日顶流》之前,是不是还没有作家写过这个题材?您是在何种契机下打算写这样一本关于互联网的小说?
石一枫:我一直对新题材比较感兴趣,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题材。据我所知,在这本《一日顶流》之前,重述中国人互联网生活几十年历史的题材还没有作家写过。之前我写过游戏电竞题材的小说《入魂枪》,但是综合写互联网发展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小说还没见过。
至于写作契机,我认为还是日常生活。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现在完全是一个网络社会。在我看来,这就是身边发生的典型变化,文学作品要映照社会的这些变化,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和书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记者:胡莘瓯这个人物身上深刻映照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变迁的印迹。他意外成为“顶流”,但是又对流量带来的关注感到恐惧和不适,从而踏上一条自我救赎之旅。请谈谈胡莘瓯这个人物形象的创作。
石一枫:我对一类文学人物非常喜爱,我管他们叫“流浪的二傻子”。典型的例子是好兵帅克,他因为天真而善良,因为善良而幸运,因为幸运而自由。
《一日顶流》里的胡莘瓯也是一个可爱的、傻乎乎的家伙。这种人的聪明劲儿往往用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上,对人则全无心机。和帅克的不同在于,他流浪的所在不仅是广袤的大地、命运的勾连,同时还有一个深邃平行的虚拟世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他的流浪史也是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假作真来真亦假,只把他乡作故乡,因果更加旁逸斜出,难以把握,既然现实冷漠不可捉摸,胡莘瓯的那点儿纯良就成了越发宝贵的、童话般的理想人格。面对未来,人类愈发乏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傻子”为这个物种的价值划定了最后一条护城河:做个人吧,起码别让机器比我们更像人。
记者:有评论说,《一日顶流》中主人公胡莘瓯和AI慧行的关系,类似于《红楼梦》中的甄宝玉和贾宝玉。我觉得这个说法倒是很形象也很鲜活。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石一枫:胡莘瓯和AI慧行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体两面。胡莘瓯是个善良仁义的北京孩子,他性格单纯,渴望被爱和关注,但又对流量带来的关注感到恐慌,从而选择逃离现实。慧行则是五岁的机器人,它像五岁的胡莘瓯一样纯净善良。两者的相貌、性格等都呈现出呼应的关系。如果机器人也算人的话,他们在性格上都属于单纯的那类人。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甄宝玉也是一体两面,不过似乎与胡莘瓯和慧行的关系相比,还是另外一种情况。
 作家石一枫
作家石一枫
小说家要呈现、思考新生事物的影响
记者:评论家孟繁华说,“看到石一枫就看到了当下文学的最新景观。”从关注监控技术的《地球之眼》,到聚焦电竞青年人生际遇的《入魂枪》,再到思索网络流量与自我价值之间关系的《一日顶流》,读者可以马上在您的作品中读到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可否就此谈谈您理解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石一枫:孟繁华老师的意思应该是,我的写作对社会的反映比较快捷和敏锐,我本身对这些也有独特的兴趣。
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我理解的有几个方面。一种是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之后,再将这个时代的种种投射到文学作品中。这属于回望过去的时代,作家会写出具有历史感的文字。另一种是迅速反映当下、思考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再就是书写下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或许科幻小说可以表现,但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品不太想象下一个时代的面貌。
对于我来说,更偏好写当下这个时代,因为一切事情都还没有定论,说不上好,说不上坏,说不上是,也说不上非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适合写小说,会给故事带来很大的发挥空间。
是非好坏非常清楚的东西适合写标语,不适合写小说。
记者:接着上一个问题,《一日顶流》的首发活动中您说道,“正是因为新的事物我们还没法作判断、下结论,这种小说写起来有时候像猜谜一样,有种一言难尽的创作乐趣。”可不可以理解为,这种创作乐趣是作家要去判断一件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构思出好看的故事?
石一枫:就像我所说的,因为是新生事物,一切还没有定论,所以是一言难尽的。而“一言难尽”恰恰是一部好小说应该符合的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新事物是可以写成小说的。
但是小说不一定非得判断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对新事物只能是观望,而不能作预测、作判断。这也不是小说家的工作,而是未来学家、科学家的工作。
对于小说家来说,要看到这个新生事物以及它对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以及人性的具体影响,然后把这种影响呈现出来,同时作出一定的思考。这是小说家的立场和责任。
目前AI无法替代人类原创性的写作
记者:感觉您是一名愿意深入拥抱时代变革、对一切新生事物充满兴趣又非常敏感的作家,所以才具备驾驭具有时代体温的题材的能力。您自己觉得是这样吗?
石一枫:我应该是对现实生活比较敏感、对新时代比较敏感、同时对生活充满兴趣的人。对社会发展以及身边出现的新事物我都有深入了解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到更多生活的乐趣。
我觉得这是对生活有“兴奋感”,这种人是可以写小说的。如果一个人本身对生活都不兴奋,而是充满倦怠感,那这种人适合心无旁骛地钻研生活以外的专业领域。但是写小说不是,小说本身就是研究生活的学问,作家必须得对生活充满兴趣。
记者:您的小说《借命而生》改编的同名影视剧正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播出。您也参与了编剧工作吗?觉得电视剧拍出了小说想表达的思想内核吗?
石一枫:《借命而生》我只是原著作者,没有参与编剧。剧作的改编我很满意,看到了很多惊喜。剧作保留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抗争,电视剧很好地展现出来了。
另外,小说情节本身没有那么复杂,电视剧增加了很多人物的线索,使得整体情节更加圆融、丰富。我很满意这种改编。
记者:请回答一个最近很热的问题:您觉得AI写作能不能某种程度上替代人类?为什么?
石一枫:需要看从哪个层面。我觉得现在AI可以代替人类低质量的写作,就是缺乏原创性的写作类型。
人类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原创性比较强的写作;一种是缺乏原创性的写作,我们经常看到的千篇一律的套路化的文章就属于这一种。我认为这种写作是很容易被AI代替的,也应该被AI代替,从而把人解放出来。
但是,真正有原创性的文字,目前看起来AI还不可能替代。将来或许可以——如果AI能够突破“无中生有”的这个界限。突破了这个界限,AI就可以写出有原创性的文字,真到那个时候AI也可以算是智慧生物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觉得人类作家也没有办法。首先是要接受这个现实,另外要学习和新的智慧生物相处。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