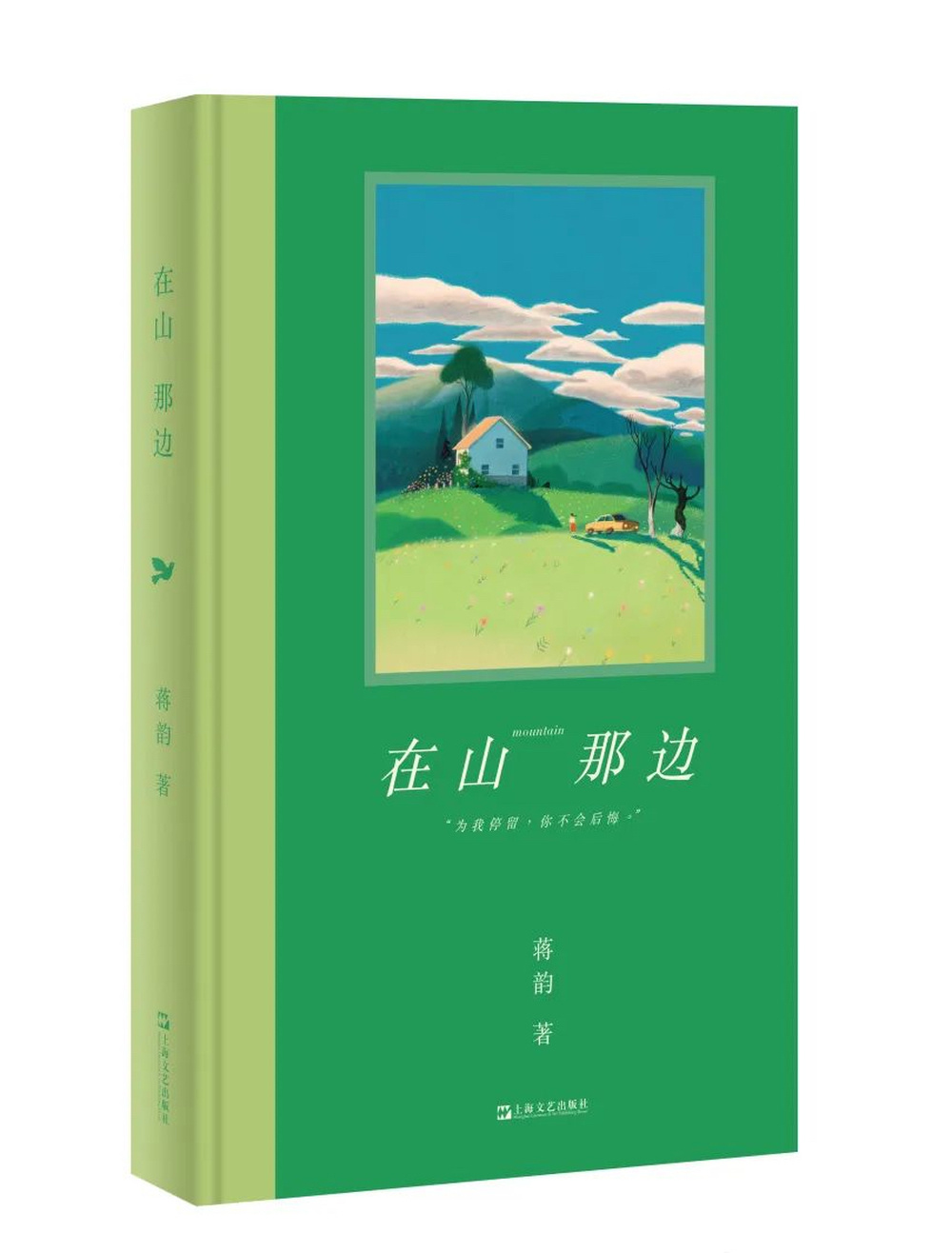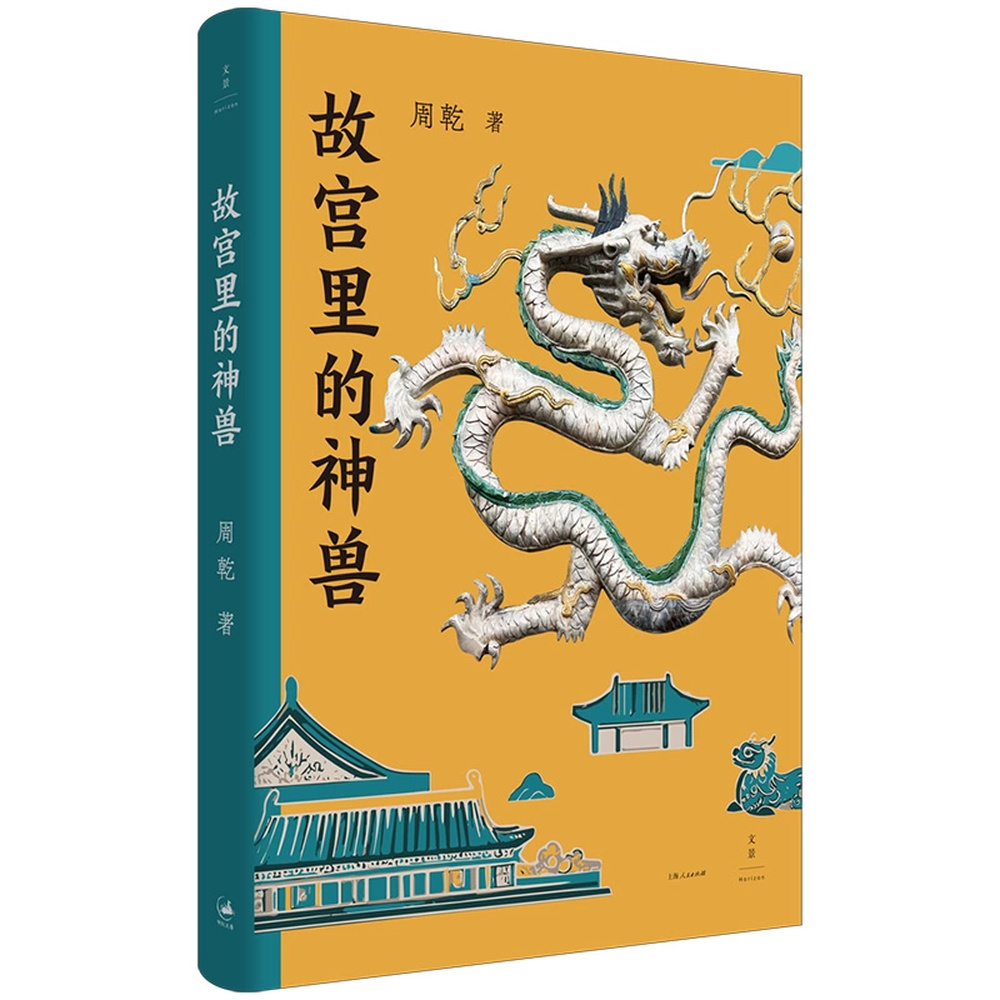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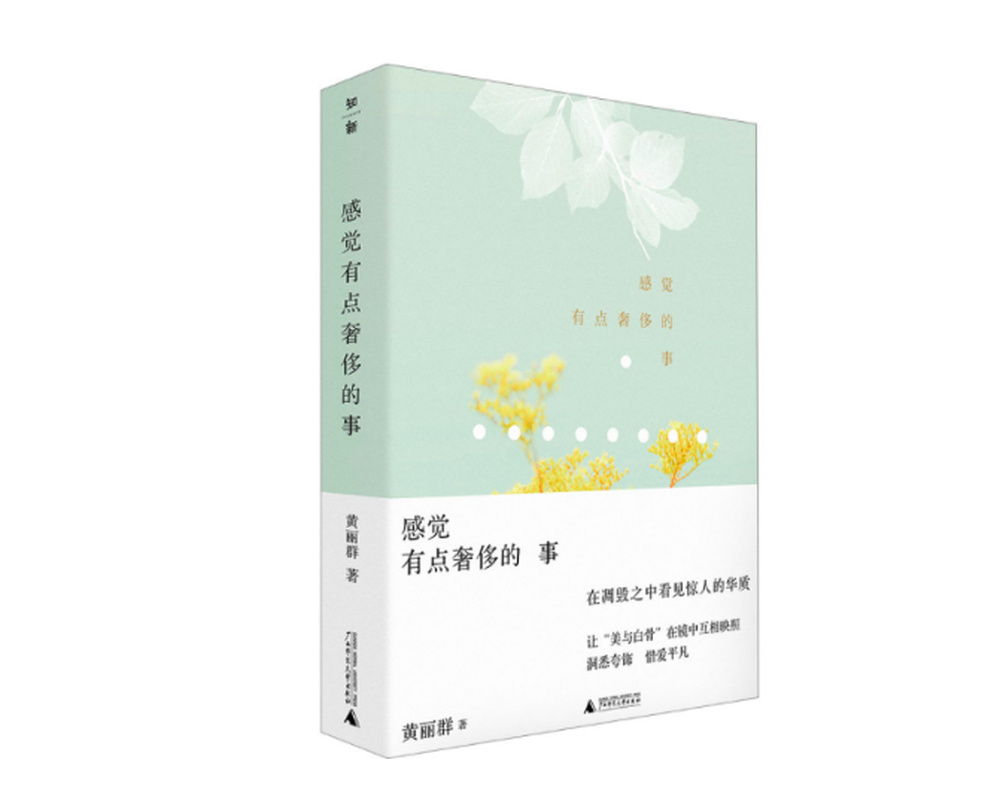
作家黄丽群的《感觉有点奢侈的事》是一部细腻描绘生活琐碎与内心情感的散文集。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充满深意的生活片段,深入探讨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如何找到内心的平衡与自由。
在平凡日常中勇于拒绝、追求内心自由、坚持自我,并将时间慷慨地给予那些非必需却滋养灵魂的美好,这是一本让人重新审视生活价值,找回内心奢侈与美好的温暖之作。
黄丽群所探讨的“奢侈的事”并非单纯指物质上的富足或昂贵,而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情感与精神上的追求:拒绝与自我呵护;内心的自由与不羁;从不讨谁欢心;将生命浪费在美好而不可用物质衡量的事物上,体验生活、感受美好。总之,这些奢侈的行为和态度,构成了作者笔下丰富而深刻的生活哲学。
黄丽群以温柔而深邃的文字,编织出的一幕幕日常中的奇迹,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封写给生活、写给自己的情书,让人在阅读中找回那些被遗忘的珍贵与美好,触动心灵最柔软的部分。黄丽群的散文风格独特,被形容为“绝对都会性格”,但她并不止步于表面的光鲜亮丽,而是深入到生活的细微之处,挖掘那些被忽视的“奢侈”。
黄丽群,生于197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曾获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短篇小说首奖,林荣三文学奖短篇小说二奖。作品曾入选《二〇一三饮食文学》及多种年度小说选本。著有小说集《海边的房间》、散文集《背后歌》等;曾以笔名“九九”出版《跌倒的小绿人》《八花九裂》等。
【精彩书摘】
家里那间书房
那时家里有间书房,书房里最早有张木头书桌,仿佛是前屋主不带走的,颜色黯淡,后来父母拿亮光漆把它刷成白色,旁边摆上立灯与旋转椅,旋转椅软绵绵的。有一面墙靠着外婆送的钢琴,除此,另一面墙做上柜子,上中层玻璃门排书,下层木门收纳。
我自己的《汉声小百科》或《中国童话》《奇先生妙小姐》并不放在这里,最早得到两本旁边不加注音符号的课外书《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也不放这里,它们在我房间。对那间书房我一开始有委婉的朦胧敌意,那里是父母年轻时一路留下来的书与杂志,还够不到上层时我有时隔玻璃门盯着那些书背上的人名与词汇看一下,并不浮想联翩,我感觉它们与我无关,倒有点像监视,里面暗示着一个父母不需担任父母的世界。对六七岁的小孩而言,一个父母不需担任父母的世界令他嫉妒。
但现在回头看就发现人长大速度其实很快,没有多久我就能够轻松打开每一层柜子,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打开门看看。有一次好像是父亲见我站在那里,问在找什么,我大概答的是“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找一本好看的给你,扫视后抽出萧红的《呼兰河传》,我很记得书皮那风沙满面的尘黄色,我说这个在讲什么,他说反正不好看你再放回去就好了。
后来我很习惯周三中午放学回家,吃过饭就去书房里,旋转椅的人造皮躺久了闷出汗,皮面里塞着的化纤棉花填料有时从破绽里窸窸窣窣地冒出来,但天凉时很舒服。我并不常想把书带到客厅或房间看。书房的窗外是一所小学满植老榕的后园(若有人从窗口悬绳而下能够直接进入校园,现在想想其实不安全),晚上看出去也鬼祟可怕,然而如果是夏初一个不下雷阵雨、干燥无云有风的下午,新绿让窗子满室生光像镶了翡翠珠母屏,蝉声神经兮兮停了又叫叫起来又忽然停,我有时伸脚搭在钢琴上,有时盘腿窝住让椅子慢速旋转,那时读了好多1970年代的过刊《皇冠》老杂志,里面有早年的三毛,登的翻译小说也多,我第一次知道纽约长岛阿米提维尔凶宅的故事就在其中一期,它的配图是一张素描像,说是按照屋主记忆与描述画出来、在屋中作祟之一的老人面容。如今我脑中还能一笔一画重现那张脸,现在描述这件事时背上发凉。
读到书架右侧一排窄长开本旧版的张爱玲是再后来的事。张爱玲习惯在每句对话前都加上“谁谁谁道”,于是见到一整页齐头并进的“这个道”“那个道”“这个道”“那个道”,我当时读了心里很好笑,觉得怎么这么笨拙。现在当然明白了好笑的笨拙的都是我。
有些书让你现在就明白,有些书让你后来才明白,都很好。有些书,你终生喜欢,这也很好。有些书你现在喜欢以后不喜欢,有些书你以后喜欢现在不喜欢,听起来好像显得次要,但我觉得它们反而更好。例如我上大学后跟所有人一样读了许多村上春树,只是忽然有一天,我再也不翻开。这些位移不一定代表昨是或今非,也不一定代表上升下降,但它们在你的路上比那些持续稳定存在者更能组成有意义的专属叙事,为什么我曾经不接受?为什么我曾经接受了?我经历什么造成这些改变?
这侧面的刻写对我来说更接近所谓作者已死:作者已死恐怕不是读者与作者的对抗与争夺,不是完全割开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也不真是那么开放由阅听者独占文本诠释(还记得那个网络上发生的真实笑话吗?某甲说:“作者在这边的意思是如何如何⋯⋯”某乙回嘴:“你把文章读完了吗?”某甲说:“我就是作者。”),而是各种作者的意图与各种作品存在于世的客观意义,成为读者理解与锚定自己的坐标,这坐标在你身上的连贯方式独一无二。作者在这里并非撤退,而是遭到消化与分解,至于消化这件事无论荤素,当然必须来自某些死,你读过的一切形成你的时间。
不过我也想,这会不会是因为自己也同时写作而产生的反抗心呢?但我也要同时申辩:毕竟每个写作者多半都是读者出身,我的“读者历”也不能说浅的。很长一段时间,读书与写作被认作双生子,或者至少是兄弟姐妹,好像爱看书的小孩作文分数就高,或作文分数高大家就问你是不是读很多课外书?其实想想我小时候读这些恐怕并非早慧,而是孤僻孩子打发时间的少数娱乐选择,如果生在今天,我大概不会成为有阅读习惯的人,网络如何改变知识的近用与累积方式、思考的回路与反射如何被弯折,也已不算大惊小怪的新闻。现在我总是对人说,喜欢书就喜欢,不喜欢,又怎么了呢,世上还有花鸟人兽,有泥有矿有皮球有虫,都很不错。
后来从小时候住的地方搬开,经过几个住处,近二十年才减少移动,过程中一路地买书丢书丢书买书(丢得最可惜的还是那批《皇冠》老杂志)。有时我坐在书架前研究自己去留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有些是一直想读但还没读,有些是带有所谓感性价值,但后来我发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当我阅读它们,我也会同时强烈感到说话与书写的愿望。这些作品未必都是客观意义上的经典(有时太好的东西反而会压垮你,堵住你),但它们怂恿,煽动,勾引,拿手肘顶顶你要你也对世界举手发问。我从小没有预期自己要走这一行,而这几年也愈来愈说不明白写作到底有什么道理好说或者算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向来也很反对某种将艺术与创作者神圣化的倾向,但如果这当中,有一件好事,或许不只在作品本身,而在于作品如何激起更多更多春夏秋冬的表达,这些表达有些我喜爱,有些我无感,有些我十分十分地厌恶,可是当它们齐聚,显得这样庄严。
编辑:徐敏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