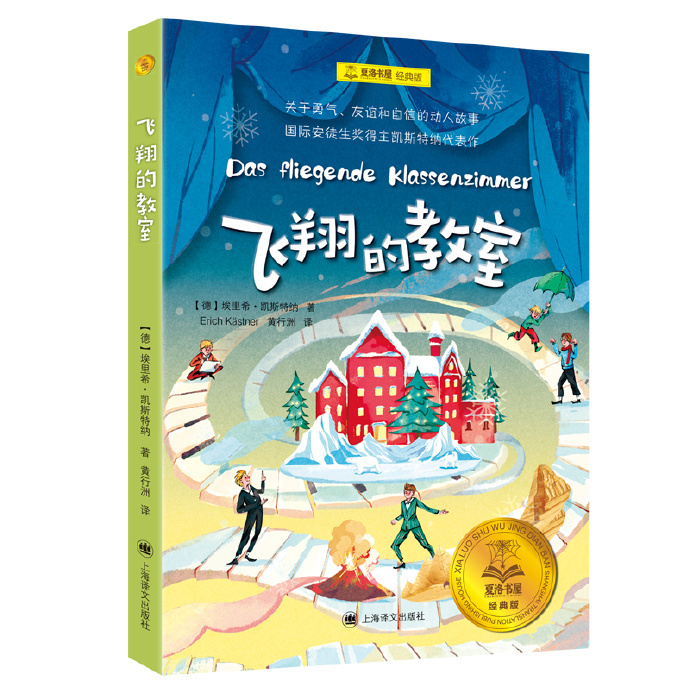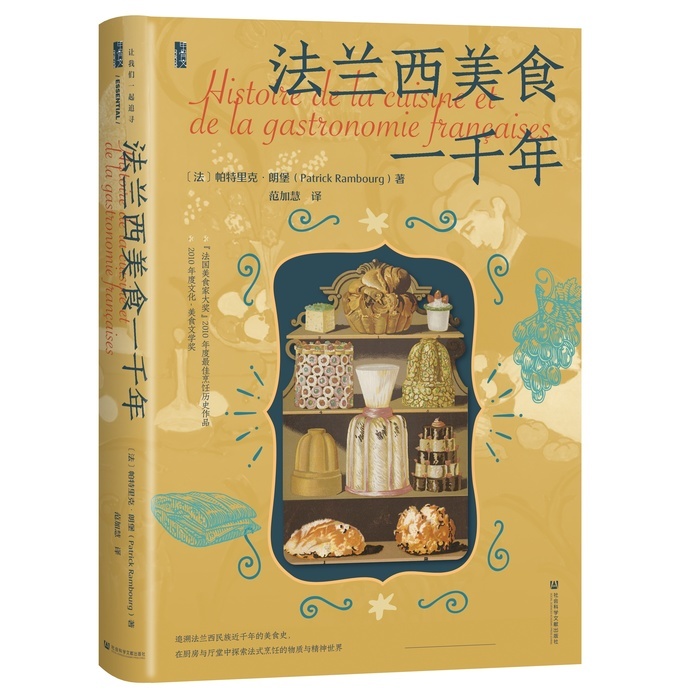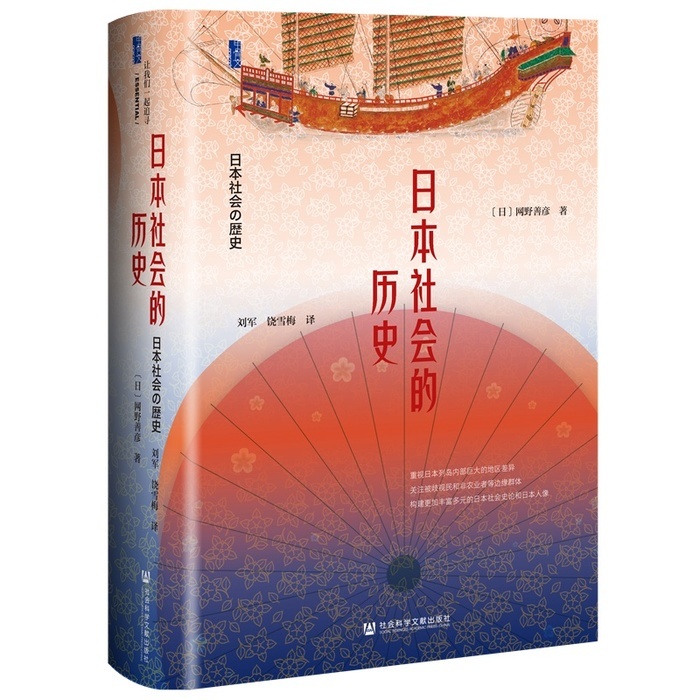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苏东坡临终情状,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如此记述:“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世。
“湛然而逝”足见苏东坡对死亡恐惧的彻底消融,对生命意义的透彻理解,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读《苏轼诗词文选评》至此,令人感动不已。这种感动当然来自苏东坡的人生境界,也来自读这本书时累积酝酿起来的情感。一本注解、评论苏东坡作品的书,能让人获得这样的阅读体验和情感波动,说实话,十分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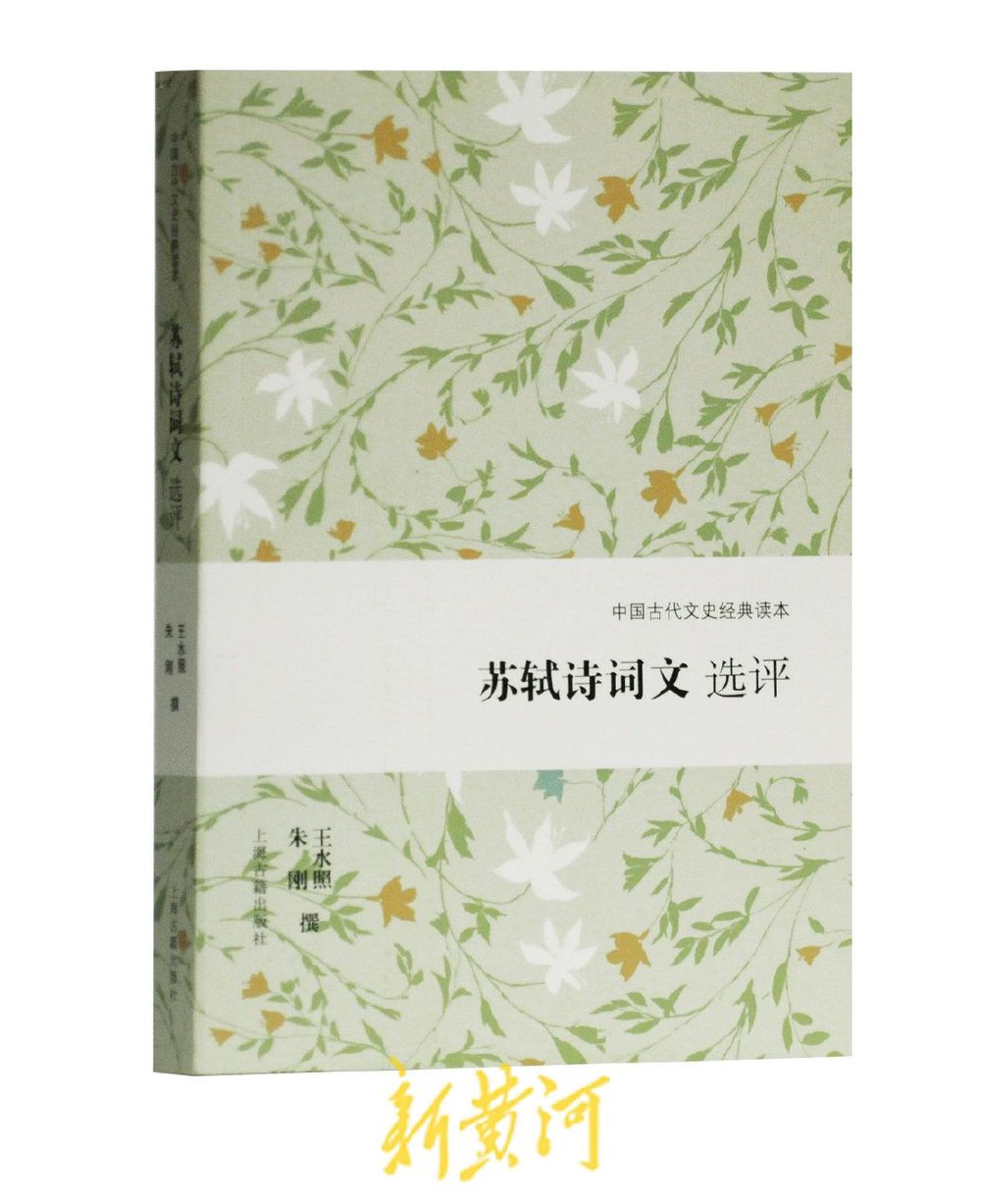
《苏轼诗词文选评》是以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和框架,将作品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归入不同的人生阶段,如此则可以清晰看到苏东坡不同时期的不同创作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除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细致分析这些作品,更结合了苏东坡创作时的具体人生境遇,甚而尽力“复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历史现场”,如此多维度解读,传递出了极为丰富、立体、深刻的认知。
这其实是极见功力的一种作品解读形式,是在对苏东坡整体人生及其所处时代的深刻认知并融会贯通后输出的一种解读。如对苏东坡幼时的“时代氛围”,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安定的时代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氛围,使范仲淹、欧阳修等一代士人不再满足于那种只随实用而转移的政治,认为那是毫无理想可言的“苟且”政治。他们要求“通今学古”,建立宋代的新儒学,按照新儒学的理想进行政治制度的建设,并鼓唱士人的“气节”,按照个人的道德良心和他信奉的学说来进行政治和文化活动,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以“道”自立,壁立千仞,绝不阿合苟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激发着幼年苏轼的人生志向。而正当苏东坡在科举考试中旗开得胜,春风得意马蹄疾地步入仕途,就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二十七个月,生命的无常和苍凉也于是进入他的作品中,著名的“人生到处应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就诞生在这个时期。
此后,对著名的新旧党争、乌台诗案等等,书中当然都有叙述,而且都能以寥寥数语切中肯綮。书中提到苏东坡给宋神宗的万言书,是当时反“新法”的奏议中最系统、完整的一封。而在旧党得势后,苏东坡对司马光的很多做法依然不认可,并耿介直言,可见其“独立之思想”。
正是这“独立之思想”,让苏东坡特别反感思想文化上出现的独断局面。熙宁六年(1073),朝廷又设立了“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如此一来,“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苏东坡认为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只能起到扼杀文学的作用,因此极力反对。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苏东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苏轼诗词文选评》将诸如《答张文潜县丞书》《上神宗皇帝书(节录)》等均收入并细致分析,并以此为切口,更真切地让我们抵达了苏东坡的“创作现场”和“历史现场”。
 话剧《苏堤春晓》剧照,图片来源见水印。
话剧《苏堤春晓》剧照,图片来源见水印。
至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苏东坡的澹荡、豁达,书中当然也有精彩分析。《六月二十日夜渡》写于苏东坡元符三年(1100)渡过琼州海峡赴大陆之时。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对苏东坡来说是又一次新生的标志。所以,诗中前四句(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以排比的句式对偶而下,一气呵成,似是以活泼欢快的节奏唱出生命澄澈的欢歌。一次一次悲喜交迭的遭逢,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终于呈现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此后两句(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可见,甚至儒学圣人乘桴浮海的那份道德守持也被超越,苏东坡在大海上听到的是民族文化始祖轩辕黄帝的奏乐之声。来自太古幽深之处的这种乐声,是混沌未分、天人合一的音响,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本身的完满和谐,它使东坡老人又一次从道德境界迈向天地境界。因此,最后两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顾这海南一游乃是生命中最壮丽的奇遇,虽九死而不恨。这是政治上的自我平反,也是人格上的壁立千仞,更是以生命之歌融入天地自然之乐章,成为遍彻时空的交响。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