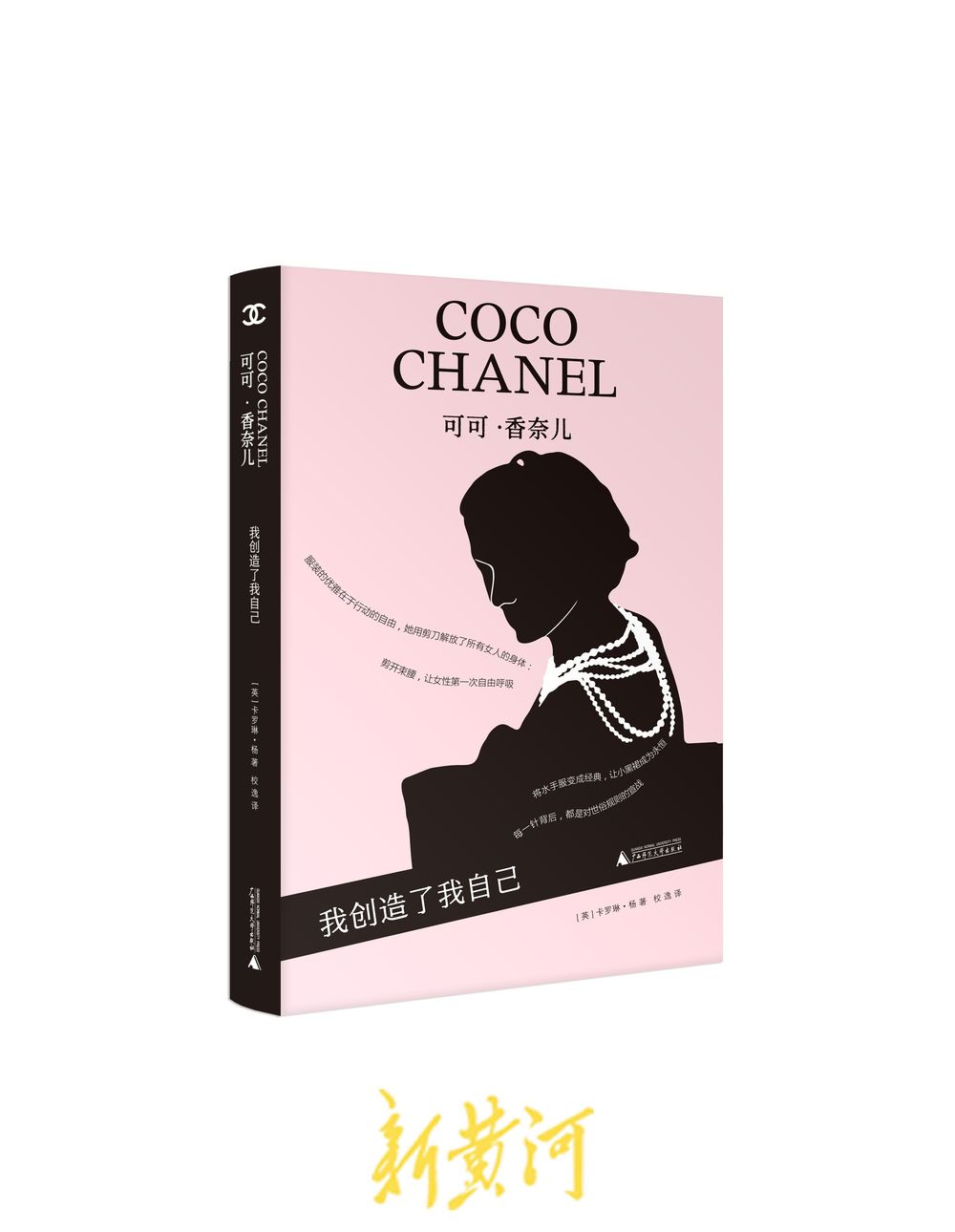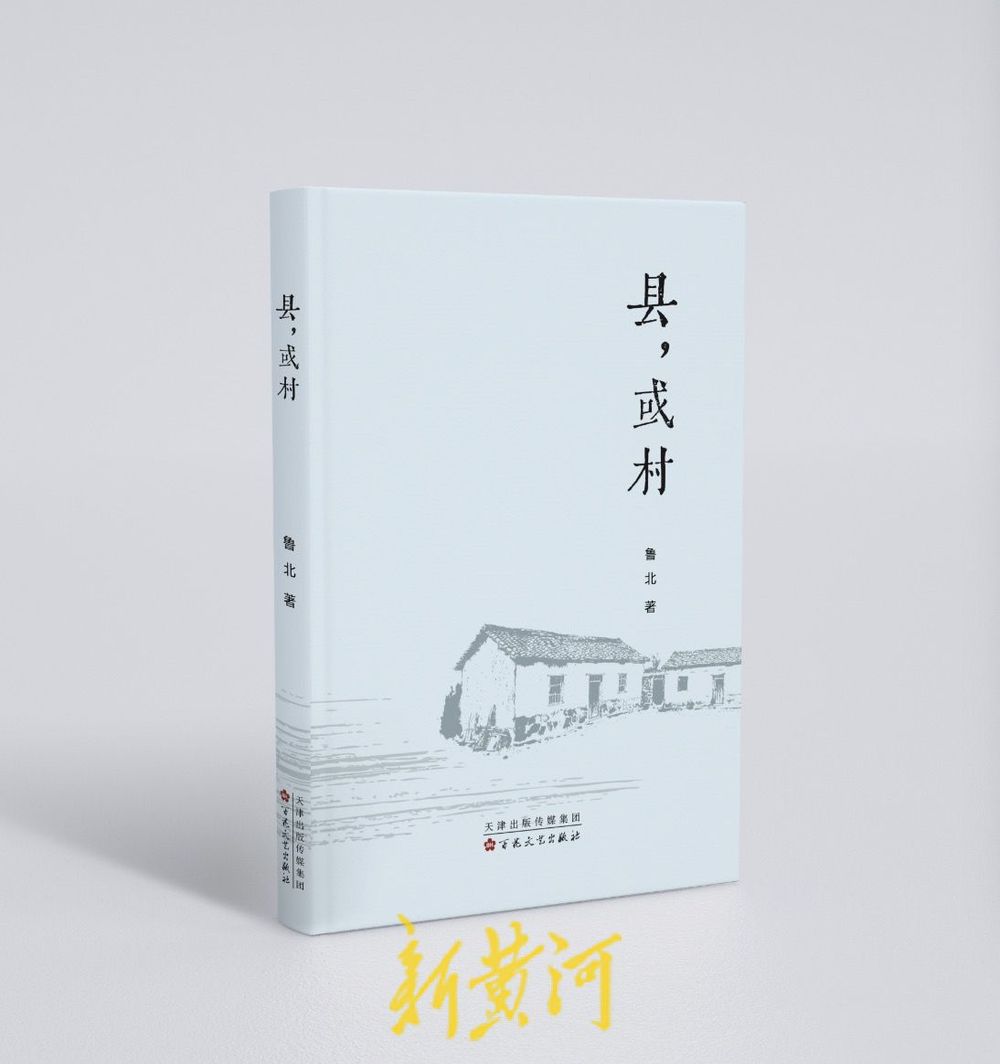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当年我在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讲题为‘随风远走’,当我在电脑上敲出最后一个句号,就该和这部作品告别了。”阿来将《尘埃落定》比作自己的“大儿子”,言语间带着父亲般的温情与洒脱。这位曾将科幻杂志推向百万销量的主编,在文坛却以“外星文明”的姿态重构着汉语写作的疆域。
二十五载光阴流转,这部描绘末代土司家族兴衰的“藏族史诗”早已超越地域与时间,在文学苍穹中划出一道独特轨迹。 2025年8月17日,《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二十五周年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阿来与毛尖、黄德海、曹元勇三位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经典重生的思想碰撞,分享会由“阿来书房”主理人阿丽丽主持。

文学史上的“外星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语惊四座:“阿来是文学史上的’外星人’。”她翻开书页,念出那个著名段落:“当一个土司多么好啊!要不是我只是父亲酒后的儿子,这一刻,准会起弑父的念头。”在毛尖看来,这种将激情置换“弑父”的书写,恰似外星文明对地球规则的颠覆性命名——爱欲、死亡、权力在阿来的笔下获得全新语法。当其他作家在既定规则中写作时,阿来直接改写了规则本身。这种异质性使《尘埃落定》历经25年仍如“悬浮的外星飞船”,持续向地球文学放射能量波。
评论家黄德海回应了毛尖“外星人”的论点,固化的土司制度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傻子”,他的眼里世界是全新的,叙事也是这个全新的视角下完成的,即苍老的灵魂拥有了一具年轻的躯体。他又从变化的维度拆解了《尘埃落定》不朽的密码,当鸦片战争轰开国门,这个被视为愚钝的年轻人却以最本真的眼睛刺破迷雾:众人疯狂种植罂粟时,他改种粮食;父亲谋划土司传承时,他预言“你是最后一任土司”。在黄德海眼中,这部小说恰似“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东方寓言。
出版人曹元勇以《尘埃落定》的“28年出版史”为坐标,强调作品经过了数代读者的检验仍“越来越坚挺”,揭示了经典的本质是抵抗时间熵增:“至少从时间的角度来讲,这本书仍然是非常新鲜的作品,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什么是一本新书?你第一次碰到它、打开它,而且发现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开卷以后收到语言的震撼,从而对这部作品爱不释手,这就是一本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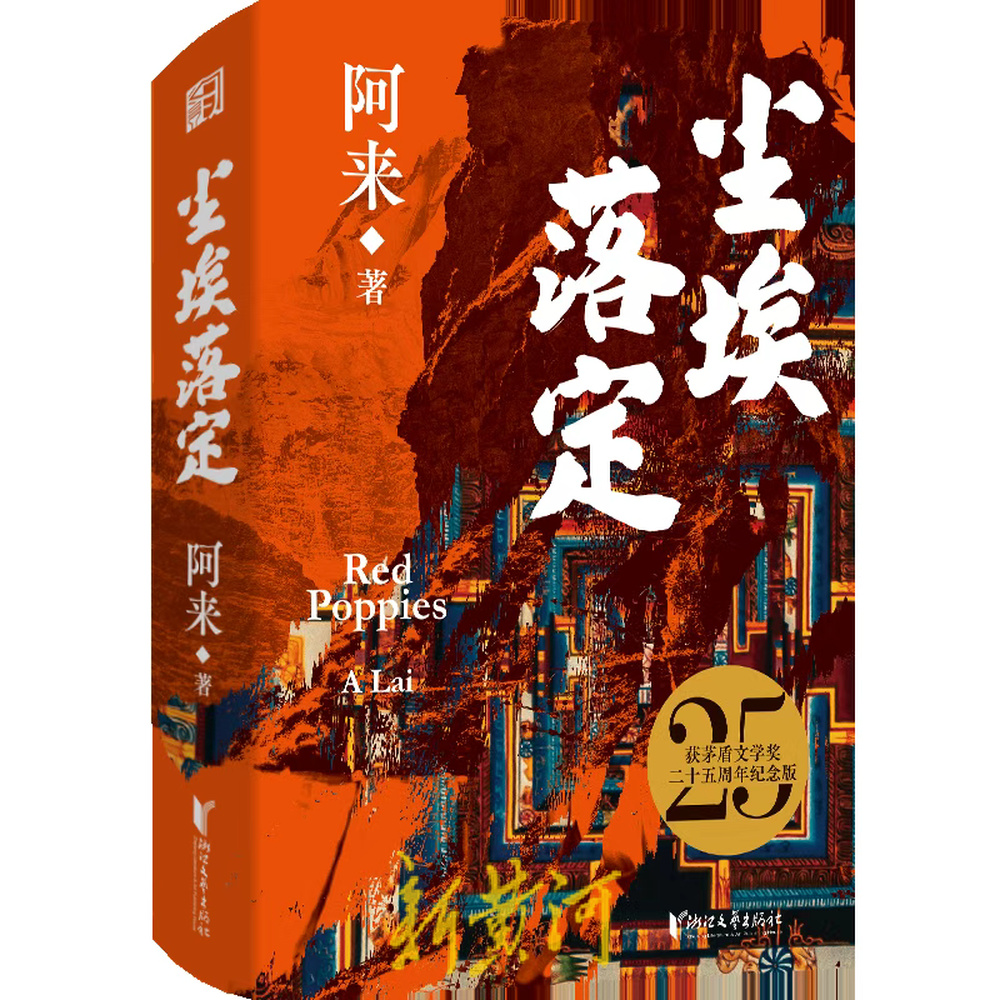
慢不是落后,而是让语言在时间中发酵
当主持人抛出“傻子智慧与时代速度”的命题,现场展开关于生存节奏的哲学思辨。阿来以林则徐贬谪日记为喻,揭示速度的本质:今人4小时穿越乌鞘岭隧道却一无所见,林公徒步7日反记录“五户人家三棵杨树”。他强调写作是对语言的绝对臣服——“当敲下小说最后一个句号,就该告别”。在高效时代,他捍卫“骑毛驴的权利”:慢不是落后,而是让语言在时间中发酵,正如《尘埃落定》中罂粟花开时,二少爷选择种粮的“滞后智慧”。
黄德海聚焦文本的时间工艺:小说以“慢速语言”讲述土司制度30年崩解,恰似用四三拍华尔兹节奏演绎革命进行曲。他揭示《尘埃落定》的“降速陷阱”:藏汉语法杂交创造语言陌生化,迫使习惯速读的大脑重启——读者无法预测下一句,如同解码外星电报。这种被迫的慢正是对抗“爽文时代”的文学抗体。
毛尖却犀利指出二少爷的辩证速度:“他预言土司灭亡快如火箭,改种粮食的决断超前如先知。”这种以慢表象实施快超越的智慧,在出版人曹元勇那里获得共鸣。他从媒介进化史切入:电子阅读器日读百页的效率,不敌纸质书开篇“铜盆洗手”引发的震颤。他以登乌鞘岭遇暴雨的亲身经历,阐明环境决定节奏:“想慢赏曹家庄,车却飞驰而过;欲驻足山顶,冰雹逼人狂奔”。出版人直言快慢无优劣——当年轻人刷短视频解构经典时,他坚持“十日读《战争与和平》才是顶级生命投资”。
好小说最珍贵的语言机理无法影像化
谈及小说跨的媒介旅程,阿来视影视改编为"平行宇宙的诞生":原著完结即永恒封存。他坦言对改编的影视“没有任何要求”:“好了是你的,不好也是你的,跟我没有关系。”与写作不同,拍戏可以将叙事顺序打乱,这种“四面出击”的能力是写作者无法具备的,因此他只想在文学世界中深造。毛尖则直指改编剧的“去草原化”缺憾:汉化美学消解了草原血脉;伦理正确的处理更掩盖了原著中“为美色公然抢夺”的生命血气。“当二少爷临终独白‘让我再来此地’的震颤被删改,小说50摄氏度的体温就降成了冷淡风。”
黄德海道破艺术转化的本质:“好小说最珍贵的语言机理无法影像化。”他提及苏联七小时的《战争与和平》仍难替代托尔斯泰的文字星河。改编本质是“借尸还魂”——影视需另创叙事核心而非复刻文本,否则终成二流仿品。
曹元勇坦言“期待电视剧带动销量”,却以话剧版成功印证文字力量,当二少爷躺在血泊中仰望星空,念出“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时,剧场涌动的热泪恰是文字力量的延伸。他借昆德拉和影视化对着干的案例佐证:《尘埃落定》中铜盆洗手、星空独白等细节构成的“防弹衣”,才是经典对抗时间的真内核。
若小说蕴含启示,也应是关于人类普遍困境的隐喻
面对年轻读者将土司制度解读为“职场内卷”,阿来认为“不是一定要这样概括年轻人”,但指出当下读者“过于关注眼前处境”的倾向。他举例说明书店现象: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摘取“职场智慧”的流行读物,实则是功利化阅读的缩影。他提出作品应作为“远方镜像”存在:若小说蕴含启示,也应是关于人类普遍困境的隐喻,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以幽默反问消解职场焦虑的局限性:“要开解的东西多了,最能开解的是号称解万愁的《佛经》”。
黄德海借古希腊“血气”概念回应时代焦虑:“真正的躺平需要勇气,二少爷的智慧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当95后在二少爷身上看见“打破旧秩序”的象征,毛尖则提醒警惕简化:“小说中银行叙事突转厕所描写,藏人晕高的细节,这些抵御爽文的慢节奏才是精髓。”
分享会落幕时,主持人阿丽丽望向满场读者:“真正的经典从非高阁古董,它在我们每一次讨论中获得新生,启发着我们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保持清醒,寻找生命的意义。而我们既是生命的见证者,也是续写者。”《尘埃落定》依然如外星造物般悬浮于文学苍穹——当土司官寨的尘埃在时光中飞舞,每个读者仿佛都成了麦其家的二少爷:以新鲜眼睛重审世界,在慢与快的辩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