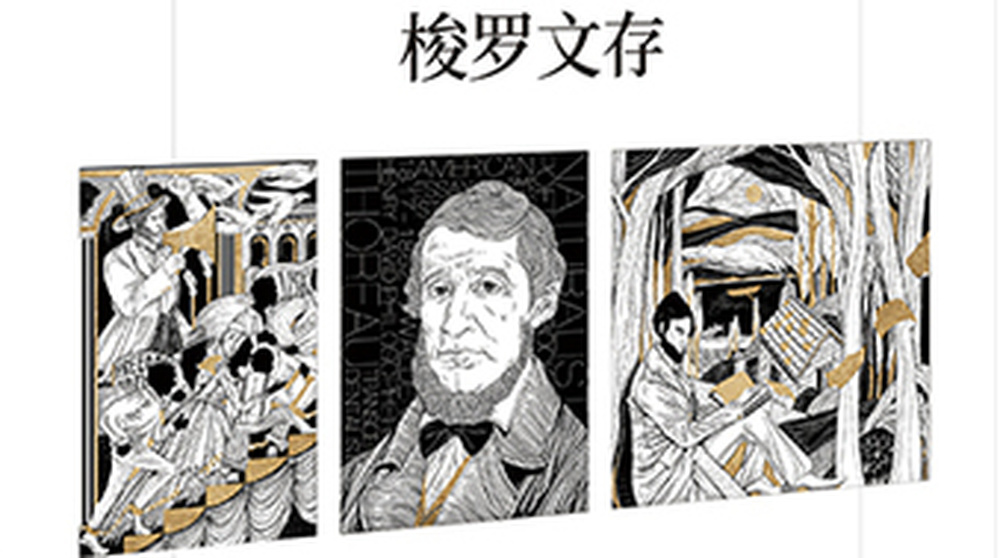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徐敏
近日,著名作家鲁敏的中短篇小说集《不可能死去的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集共收录其五年来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的中短篇小说,包括《灵异者及其友人》《暮色与跳舞熊》《不可能死去的人》《无主题拜访》等九篇作品。小说关切那些在夹缝中喘息、在尘埃中翻滚、在无常的命运歧流中泅渡的普通人。
在人工智能引发写作替代忧虑的时代,鲁敏一如既往地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独特的叙事风格,持续探索当代人复杂幽微的精神世界与生存困境,书写“不可能死去的人”,以及他们活着的姿态。《不可能死去的人》不仅以深沉情感讲述角色的生存故事,更彰显了文学创作中“人”的主体性与不可替代性——人,在文学中不可能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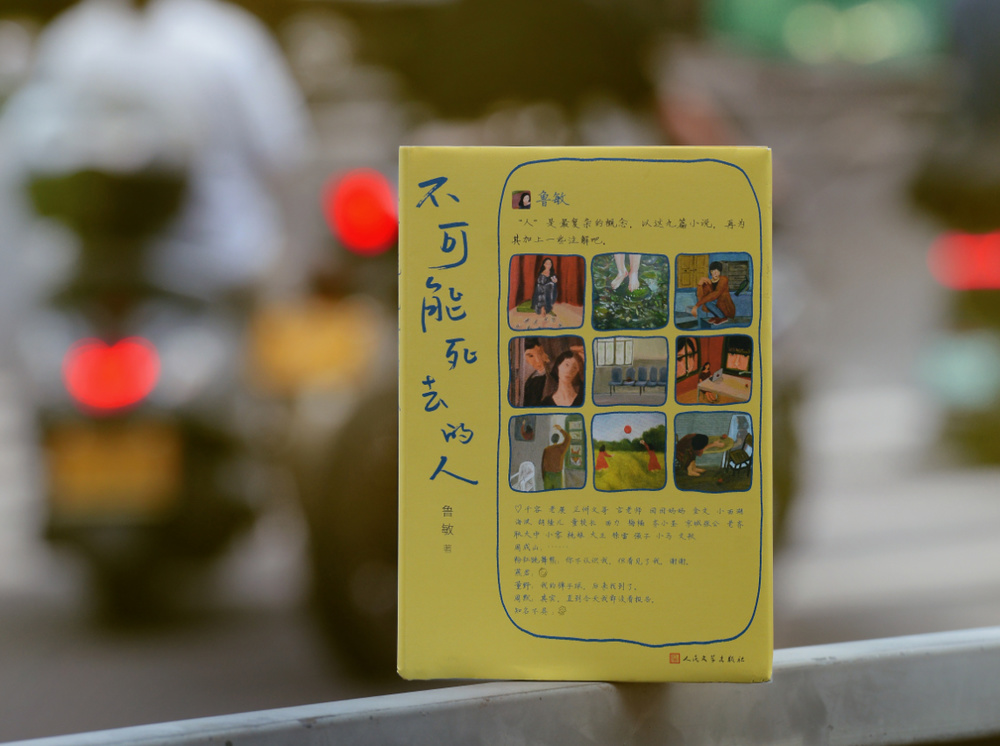
与人有关的面孔、故事和声音
记者:请先谈谈《不可能死去的人》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的结集过程,以及为何选择《不可以死去的人》这个单篇的篇名作为书名。
鲁敏:《不可能死去的人》是我的一部中短篇小说合集,共收录了9篇小说。这些小说均创作于过去五年间,当然这五年的创作不止这些,我精挑细选了这些与当下人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篇目。
世事纷繁热闹,很多时候“人”本身反而不被看到。人们被贴满各种各样的标签:拖延症、躺平群体、I人E人等,简单机械地处理自己的生活和情绪。从这个角度讲,渺小而具体个性的自己反而被忽略。尤其近两年,AI、智能搜索等话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这种扑面而来的技术主义的胜利更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人,给人带来危机感。然而这些也从另一角度减少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和讨论。
我认为,世界上最触动我们的,最不可磨灭的,还是人,以及与人有关的故事、面孔和声音。“不可能死去的人”指的不是小说或现实里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天地之间弱小的、随时在死去的,但在广泛意义上又生生不息永恒存在的人类。
在人反复被标签化、被定义的背景下,在人们热情欢呼和拥抱技术的背景下,《不可能死去的人》这部小说集呈现了渺小的、软弱的、四季日常中人的样貌。
记者:我个人非常喜欢《暮色与跳舞熊》《寻烬》这两篇,请谈谈这两个故事最初的题材来源灵感。
鲁敏:我决定写什么人物,或者设定什么人物成为小说主人公,是很偶然的过程。
《暮色与跳舞熊》这篇的创作缘起是,我们经常在游乐场或者公共空间看到人扮演的跳舞熊或者其他动物、人偶。他们在商场里亮着可以扫二维码的肚子,或者摇摇摆摆地跟小朋友合影。他们不是那种游戏、浪漫、狂欢性质的人偶,而纯粹是谋生的一个人偶造型。不过,日常我们看到人偶会觉得是童话般的存在,会有某种轻盈、浪漫的理解。而我看到这个人偶的时候在想,跳舞熊的形象和里面的人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由此,我对这个看不到面孔、身体也被遮蔽的人产生了书写的兴趣。
至于《寻烬》这一篇,最初的构思则来源于南京确实有一个百货市场发生过火灾,当然小说中具体人物和故事均是虚构的。百货市场是烟火气十足的场所,是一代人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消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互相揶揄、妥协、巧斗又热闹非凡。可以说,这篇小说寄托了一代人大市场的消费记忆,是人们对那种相对传统的更具人的气息的消费模式的回望。
 作家鲁敏
作家鲁敏
生命、年龄经验带来新的写作题材
记者:您在活动中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慢慢发生了变化,这些也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作品中。这是不是避免了写作会出现自我重复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您用何种方式保持每部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
鲁敏:40岁的时候我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荷尔蒙夜谈》,选了一个略有点刁钻的中年角度,因为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往往比较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觉得智力啊才情啊这些非常重要,但40岁前后那个阶段,我认为身体本身的因素常常是被忽略的,它其实非常重要,一个人在某一天的情绪和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很大的事情。比如,某个人这一天微妙的心境可能会影响他在某个大型会议上的表现或决策,比如我们看《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许多历史细节。所以那一阶段集中写了一批“荷尔蒙”。
如今我到了50岁,荷尔蒙开始退却,绝对的理性、唯物主义、成功主义等观点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似乎有一种“初老”感,也不再追求夸张激烈的戏剧性,我想写人与时间的关系。所以很喜悦的是,时间的推移会给作家带来新的写作技术的哺养,也会帮助作家在某个阶段发现要书写的重点。
所以说,生命经验、年龄经验会给作家带来新的写作题材,尤其是作家个体年龄变化与时代发生化学反应、物理反应。所以我感到作家如何避免自我重复,这会有天然的时间来帮助我们。
记者:一如既往地,在这本《不可能死去的人》中可以感受到,您还是能精准地捕捉并书写那些幽微的情绪。在您看来,作家将不可见的心理活动转化为可见的、富有张力的文学情节,最关键的能力是什么?
鲁敏:写中短篇小说需要非常谨慎,所以五年时间才集结了这9篇小说。对于听闻的那些别人的故事或者新闻事件等,我会非常苛刻地选择题材。现在写作时,会考虑这篇小说、这个故事会不会得到读者的共鸣和反馈。
我现阶段的小说中,人物的年龄分布跨度比较大,既有《暮色与跳舞熊》中的青年插画师,也有《寻烬》中的老阿姨。写作时,我会尽量跳出自我经验去把握外面世界的某种情绪,把握外部世界与时代情绪的公约数。
上次在上海书展做交流时,作家路内聊起我本书,认为它是抓到了“时代的拐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城市、乡村都在拐弯,作家需要找到这种共鸣点,找到更多读者和人类的共鸣点。
记者:我看到有读者说,从《不可能死去的人》这部小说集中读到了契诃夫的味道。请问有哪些以写作短篇小说驰名的作家对您有所影响?
鲁敏:“读到了契诃夫的味道”是读者的谬赞了。
除了传统经典,我也很关注当代世界文坛各个语种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称之为“新经典”,即将要成为经典的作品。比如,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蒂姆·高特罗《信号》,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被困住的人》等。
短篇小说具有生猛、活泼、灵动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语种的作家是如何用小说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国家民族、空间与人的关系。
AI时代,依然相信人的心的力量
记者:您认为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小说家最重要的使命或责任是什么?是记录时代、提供文学滋养,还是探究人性的永恒困境?
鲁敏:现在我们可以轻易提出场景人物与情绪需求使用AI生成一幅画,AI可以做得很完美。即便如此,依然有画家在一笔一画地绘制一幅画,也依然有摄影师在一帧一帧地拍摄图片。作家就是从文字角度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一字一句的,用虚构的方式留下人的面孔、声音、经历和故事。对于文学来说,虚构所折射的正是最大的真实。
这种记录未必那么及时,但是会像提纯的香精一样,散发出人在这个时代留下的气息。写作不是一个热闹的行当,也应该有艺术家、作家、诗人持续地做这件事情。
记者:近一两年我们一直在讨论AI写作,到底AI写作能不能够替代人类,多数作家给出否定的答案。不过不可回避的是AI确实替代了很多人类写作,甚至已经有文学奖颁给AI(当然背后也有作者操控AI)。您觉得写作者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冲击?
鲁敏:我用一两个小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是江苏人,江苏宜兴盛产紫砂,当地有个紫砂博物馆,展品有几层楼,从最早的紫砂陶器,再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流变,创造性的设计与技术上的突破,都让参观者叹为观止。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看得最多的、最流连忘返的,还是最早的供春壶。它的形状不太好看,上面还有手指的印,捏得不太平整,整体非常传统,非常笨拙,但仍然强烈吸引着所有的参观者。
我认为那种原始的、朴素的,或者说背离现代性的东西,可能依然对当下的人是有吸引力的——是不是,正因为它有“人”气息。我说不好,我只是讲这么一个现象。
假设一下,如果同时出现两个版本,一是AI续写的《红楼梦》,一是重新发现的曹雪芹版《红楼梦》后40回。这两个新闻哪个更轰动?我相信,哪怕曹雪芹版带着它的破绽,它的局限,大家也还是更愿意把阅读与探求的目光放在后者。
当然我对AI的这个想法比较保守和传统。可能因为我在写作这个行业里面,对这个行业太有感情,所以我愿意选择相信人的心的力量,相信文学永远是与“心”相关的事业。
编辑:任晓斐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