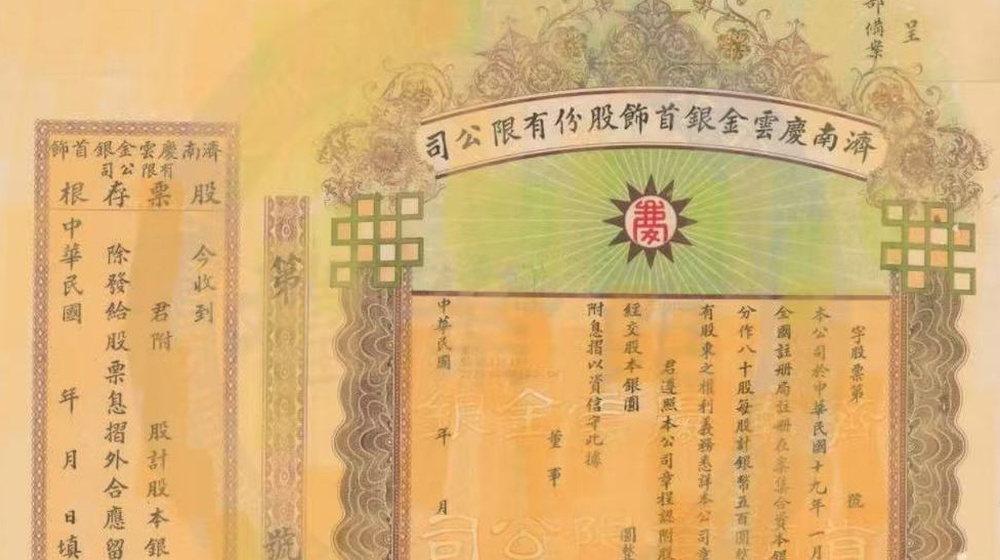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徐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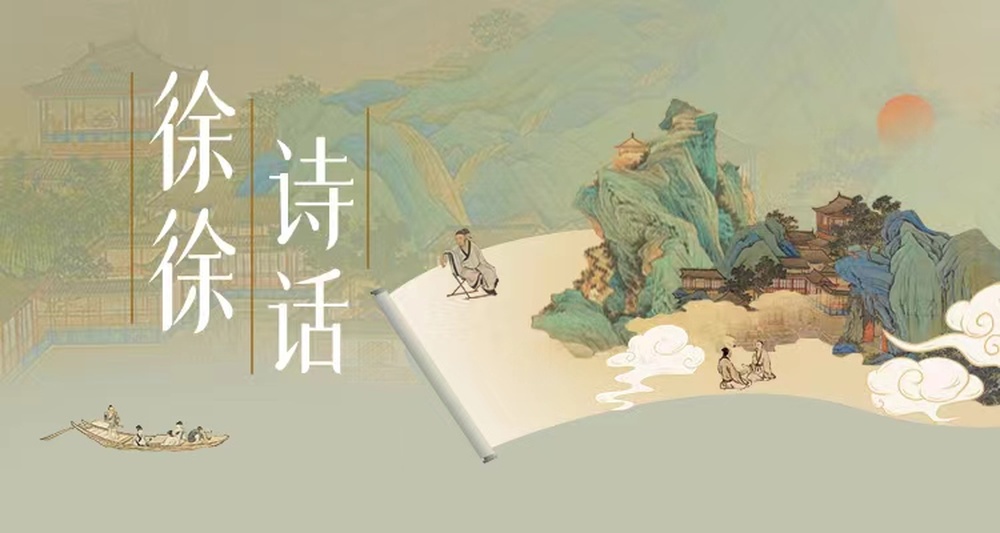
之所以说中唐之前对长安最眷恋的是李白,因为中唐时期还有一名文人,他对长安的依恋之情远远超过李白,这个人是柳宗元。柳宗元对长安的感情,可谓入心、入骨。
与其他诗人不同,柳宗元虽然祖籍不是长安,但自幼在长安长大,理所当然地将长安视为故乡以及日后生活、为官的地方。柳宗元因其父柳镇在安史之乱期间徙家吴地故而出生在此,不过四岁左右便已迁回长安。后来他在给母亲写的墓志铭《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提到:“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说明柳宗元自幼在母亲的教导下在长安读书、成长。这一时期的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后恢复平稳并且逐渐走向中兴,而“河东柳氏”又是世代为官的高门望族。可以想象,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的柳宗元,必然要走科举为官的仕宦之路。
贞元九年(793),年仅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这一时期的柳宗元,还是韩愈后来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描述形象精准:“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由此可见青年柳宗元的学识和风采。不过,也如古典文学专家尚永亮评价,从韩愈的这些用词中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已为柳宗元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柳宗元的人生经历线索比较简单。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803年,做过一段时间的蓝田尉后调回长安,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于805年参加了王叔文主导的革新运动。革新很快失败,柳宗元的政治命运急转直下,经历了永州十年、柳州四年的贬谪生活后在柳州病逝。十四年投身南荒的贬谪生涯,柳宗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长安、回望长安、想要再次回到长安。
这还不同于一般的贬谪。这次贬谪带给柳宗元的是近乎绝望的政治前景,因为不久之后朝廷还下过另一条诏令,(柳宗元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内。”这等于彻底断绝了柳宗元回京的希望,将其永久地定性为政治罪人。可以想象,这对一名年纪轻轻便科举及第、活跃在政治中心的青年官员是多么大的打击。永州十年,柳宗元的性情更加孤僻、幽独,这也是他逐渐转向山水诗文创作的原因之一。
十年后,命运再次弄人。当命运的罅隙照进一丝光芒,这丝光芒又猛然被无尽的黑暗吞噬。元和十年(815)正月,在永州艰难地度过了十年之后,柳宗元终于接到来自朝廷的返京诏书。他欣喜若狂,迅速收拾行囊踏上返京的行程。长安,他要回到长安。
二月,走到长安东郊的灞亭时,柳宗元有诗《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长安!前面就是长安了。虽然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官员,他的鬓角已经苍白,容颜已经渐渐衰老,双膝还时常微微颤抖,但他的脸上总算有了神采飞扬的痕迹。诗人把这十一年来在四千里外南荒的苦苦期盼和感慨熔铸到这两句诗中,“南渡客”与“北归人”相对,激动之情溢于笔端。诗人接着感慨,这一路走来,处处都是簇簇盛开着的春花,一切都昂扬着春天的新意。即将踏进长安城的柳宗元此时也深深相信,他的政治生命也将迎来充满希望的新阶段。

不过,这次打击来的和上次一样迅速和强烈。在长安席未暇暖,三月,柳宗元再次被迁为柳州刺史,柳州比永州还要更加偏远。这次离开长安,柳宗元真是万念俱灰。
唐朝时,柳州是生存环境更恶劣的蛮荒之地。这里盘郁着山岭河流,充塞着瘴气,空气中盘旋着雾气,毒蛇猛兽时常出没,民风也比较粗鄙。这一切,都让柳宗元感觉处于一个异质文化圈中。多年的贬谪生涯,不管经历多么蹉跎的心路历程,柳宗元必须接受这一切,然而还是难以排解对长安、对故乡的怀念。元和十二年(817)秋,友人浩初过访柳州时,柳宗元有诗作《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每次读这首诗,都能感受到这名万里投荒、孤身去国的诗人的锥心刺骨的疼痛。开头第一句就是一句很坚硬的比喻,这个比喻放在唐人的诗句中虽然新奇,但却不太流畅自然。不过读到第二句我们就明白了,山峰尖如剑锋,在这个寥落的秋日正在割着诗人的愁肠。“割”这个字狠重有力,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痛彻肺腑。这是一种怎样的思念啊。望着渺渺远山,诗人幻想着我可以化身为一千个我,一万个我,每一个我都站在山峰上望眼欲穿地遥望着长安的方向。这是一种浪漫、深邃又椎心泣血的眷恋。这种与长安的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啊。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这两句的写法奇异而又释放,让读者体会到诗人对长安不可遏制的思念之情。这两句直接启发了后世陆游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之句。
这一时期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呢?柳宗元一定也听闻了一些消息。元和年间,王朝呈现出中兴局面,尽管也还有很多问题,不过君主勤政,政坛相对清明。他的友人韩愈在长安和洛阳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进行文风改革,文坛也生出了新气象,韩愈成为文坛宗主;与此同时,白居易以平易通俗的诗歌也收获了大量读者,市井街头无人不晓白乐天。如此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政治和文化场景,柳宗元只能远远地遥望。
大概是在同一年的秋天,柳宗元还有一首《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
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
秋日午后,诗人独自登上一座荒山。登山,自然是要遥望长安的方向,不过自然是看不到长安的,只看到了西北处的融州。想来,登山遥望长安是诗人经常外出进行的习惯性活动,他或许还盼望着能有回到长安的那一天。
遗憾的是,柳宗元至死也没有再回到长安。
编辑:徐征 校对: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