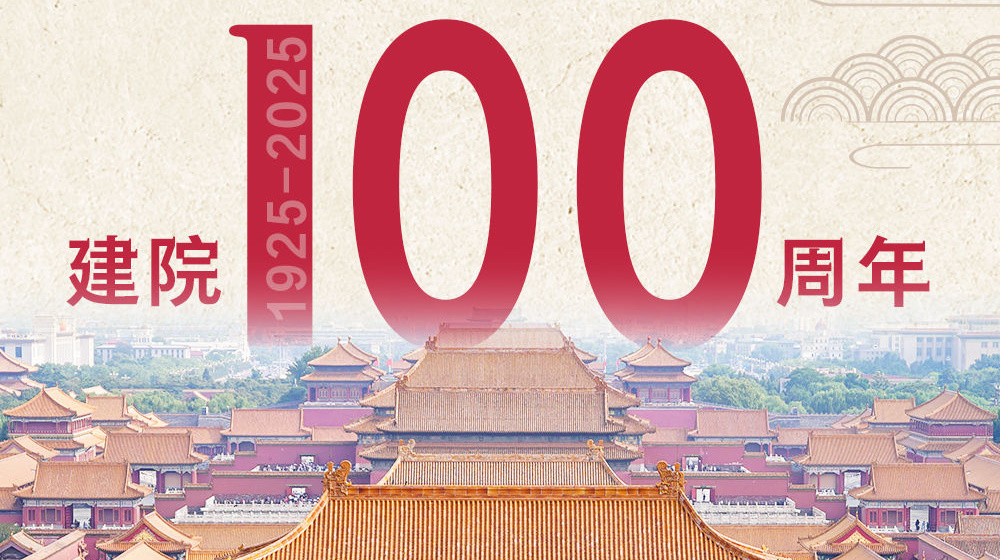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并称为“冯陆高萧”,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大学的金字招牌,也是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
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早在上世纪20年代,冯沅君就以“淦女士”为笔名发表小说,走上文坛,成为与冰心、丁玲、凌叔华等齐名的“五四”以后的第一代新文学女作家,得到了鲁迅等文学巨匠的高度评价。
1932年,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一起赴法国巴黎留学,于1935年同获博士学位。冯沅君回国后极少提及在法读书的情形,至于其博士学位论文,学界更是一无所知,深以为憾。留学法国是冯沅君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如今,这个遗憾已经被完美弥补,山东大学一位从二十余年前就开始关注冯沅君相关文献资料与学术生平的学者关家铮,托其友人在法国上下求索,终于在尘封的故纸堆中查找到冯沅君的博士论文,并复印带回国内。随后,在关家铮的推动下,山东社会科学院车振华博士和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焦宏丽博士着手将全稿翻译为中文,并正式出版,填补了空白。
近日,新黄河记者专访了在查找冯先生的博士论文并翻译出版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关家铮先生,请他讲述了冯先生尘封近百年的博士论文重见天日的传奇故事。
 冯沅君
冯沅君
与冯沅君先生的两代情缘
关家铮对冯沅君相关文献资料的关注,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关家铮告诉记者,2000年初,他在整理家中旧书刊和书信时,翻检出一些上个世纪的旧报纸副刊,“多数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剪报,其中发现了冯沅君先生的不少文章”。这引起了关家铮对冯沅君先生学术历程的一些想法,“众所周知,冯先生最初是得到过鲁迅赞扬的女作家,后来转作学术研究,一开始是正统文学的研究,如和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法回国后,她的学术研究转向俗文学。留学法国因此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节点。我心里就想:冯先生回国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术转向呢?可惜的是,由于冯先生在法国的博士论文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问题也就无法获得一个很好的回答。”
关注到与冯沅君先生相关的文献资料后,关家铮还陆续撰写了几篇关于冯先生俗文学研究和学术生平的文章,他坦言,这既缘于他对冯先生高尚品格和崇高成就的敬仰,也有一些私人的感情在其中。
原来,关家铮的父亲、著名学者关德栋教授,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教授,就是受到冯沅君和陆侃如的联名邀请。
据刘光裕《吾师关德栋教授》一文,关德栋教授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佛学院做讲师,继而又到上海佛学院做教授,“先生将治佛的成果,加上比较语言等方法,用于研治敦煌文献,所撰文章在刊物上接连发表,独树一帜,从而为敦煌学、俗文学开辟了新路径,震惊全国学术界,很快成为敦煌学、俗文学领域升起的新星,深得郑振铎先生赞赏。1947年,历史学家向达著文说:‘二十年来注意敦煌俗讲文学者,寥寥可数。今日得读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的文章,不胜空谷足音之感。’这一年,先生只有二十七岁。”
关家铮说,父亲初识冯沅君先生,正是1947年,“那一年父亲跟随历史学家金毓黻到东北参加沈阳故宫博物院等处文物的接收工作,其中有很多满文老档,父亲任翻译组组长,那时候冯沅君先生正好在东北大学任教,两人于是有机会见面,冯先生还跟我父亲说,看过他发在《俗文学周刊》的很多文章。满文老档事宜处理完毕后,父亲又辗转北京、上海、兰州、福州等多地任教,1953年,受冯沅君先生和陆侃如先生邀请,父亲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
关家铮回忆说,“冯先生邀请我父亲到山大,有一个原因是冯先生当时想在山大中文系建立起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研究的专业。而我父亲来山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母亲当时在山东大学任童第周爱人叶毓芬的助教,调山大可以让夫妻不再两地分居。在山大期间,我父亲与冯先生合作开设宋元明清文学课程,一起制订敦煌文学研究计划和助教培养计划,他们共事二十余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关家铮幼年时曾与陆、冯两位先生毗邻而居,如今数十年过去,冯先生走在路上那颤颤巍巍的羸弱身影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冯先生一辈子没孩子,但她特别喜欢小孩,常拿糖给我们吃。”关家铮还记得,冯先生家中非常朴素,经常用铁皮罐头盒当饭盒去打饭,“‘文革’中冯先生被隔离审查,从新校文史楼到宿舍食堂吃饭,要先到食堂外和其他被隔离审查的人排成一排,再去打饭,只能打五分钱的菜。”
 冯沅君(左一)和山东大学教授关德栋(中)在检查助教袁世硕进修情况
冯沅君(左一)和山东大学教授关德栋(中)在检查助教袁世硕进修情况
尘封法国近百年的论文,终于被找到
关家铮常听父亲讲冯、陆两位先生的生平轶事,包括他们俭朴的生活和勤奋的工作,当然也包括他们对学术的求索和创新。冯先生去世后,关德栋教授非常关心她遗作的整理出版问题,他在1975年2月2日致赵景深先生的信中说:“她的遗稿据侃如说约存一箱,但究竟都还存下些什么?始终还没检阅,具体情况当然也就很难说了。我曾问过关于戏曲史方面的书稿,据他说也还不了解剩了啥。当然整理也就更谈不到了。据我过去与沅君先生谈话时知道的,她当年对‘远山堂’曲品剧品一书,也作过些工作;对作家生平,也有一些史料整理;对一些剧、曲也弄过些考证。后来搞宋以后的诗歌,还有些属于副产品的小玩艺儿。对陆游诗,曾计划完成全集的校点注释(可能是‘校笺’)。至于笔记(读书札记之类)还占有较大的数量。想来她既存有一箱遗稿,应该就是这一范围;其详只能将来了解了。”4月4日致赵景深先生的信中又说,冯先生遗稿无论多少,“总还是该整理的,其中总有可为后人参考的东西在,听之湮没是工作的损失”。
耳濡目染,关家铮对冯沅君先生的资料一直十分关注。而真正开始搜寻冯沅君先生的博士论文,则是在2021年。
这一年4月9日,关家铮参加了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山东大学文学院在济南联合主办的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年会暨陆侃如、冯沅君学术研讨会。会议对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杰出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他们为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做出的重大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会议开幕式上还举行了陆、冯《中国诗史》手稿捐赠仪式。会议期间,关家铮与几位专家闲聊,大家都认为,《陆侃如冯沅君合集》之外,冯沅君先生还有一些佚文佚作,尤其是她留法期间的博士论文尚未发现,造成研究其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的一大空白,实在是一件憾事。
关家铮说,早在2000年看到冯沅君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上的文章,产生“冯先生回国后的学术重点为何发生转变”的疑问时,就曾问过父亲冯先生留法时的情况,父亲当时说冯先生留法期间曾师从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而伯希和长期以来被视为盗取敦煌宝库的“文化强盗”,藉此之故,冯先生数十年来几乎不提自己在法国的留学经历。关家铮说,“但在私下场合,她还是和家父谈起她在法国所做的研究,以及留法经历对她学术生涯的影响。冯先生提供的这些线索为我们日后搜寻她的博士论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综合这些信息,关家铮先是请一位曾留学山东大学的法国朋友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查找相关线索,后又托人查找冯先生留学期间的学籍和论文,但因为巴黎大学改变比较大,一时很难找到,“最后帮我找到冯先生博士论文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单志斌博士。2022年春,他利用在法国学习的机会,上下求索,不辞辛苦,顺利查到冯先生的博士论文并复印带回国内,奠定了后续一切工作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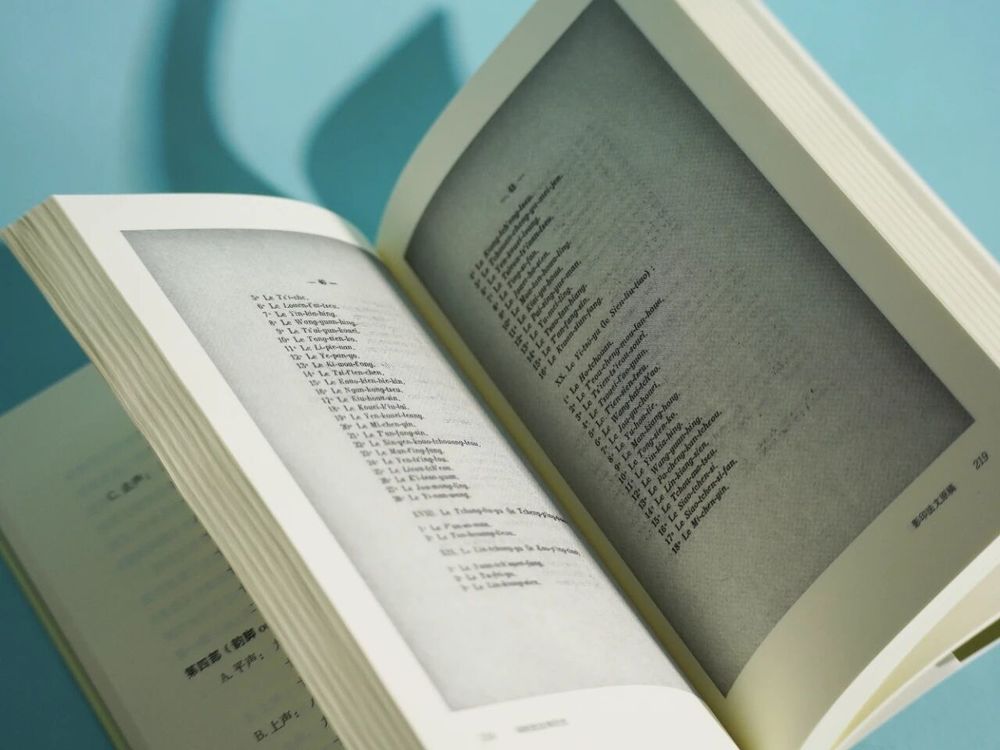 影印法文原稿
影印法文原稿
融通中西学术交流的重要文献
随后,在关家铮的推动下,系列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展开,山东社会科学院车振华博士和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焦宏丽博士着手将全稿翻译为中文,并写作《新发现的冯沅君博士学位论文〈词的技法和历史〉——兼论冯沅君的词学研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多家网站转载,引起了热烈的学术反响。关家铮与其学术团队继而将中文译文多次仔细审校,后附法语原稿影印,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终于将这部尘封已久的学术遗珠呈现给学界与大众读者。
冯沅君的博士学位论文用法文写作,标题为LA TECHNIQUE ET L'HISTOIRE DU TS’EU,中文译为《词的技法和历史》,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是巴黎大学文学院。论文署冯沅君的本名冯淑兰(FENG SHU=LAN),身份为原北京大学讲师、女子师范大学文学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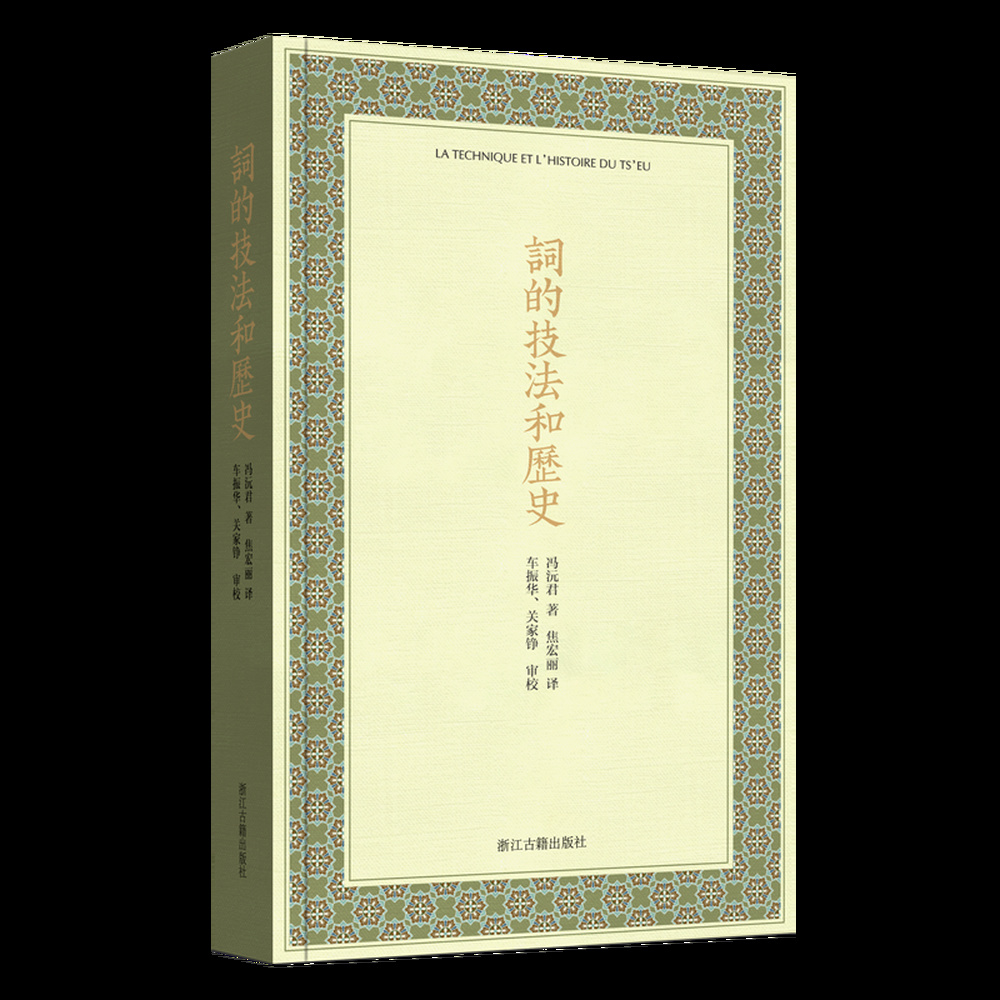
《词的技法和历史》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词的词牌、韵律、修辞等基本知识和作词的技法规则,第二章至第五章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从唐末五代到清代的词学发展史,并对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简要论述。正文前有“前言”,后有中文索引,以及用法文写作的参考文献(列出了主要词人的著作及版本)。冯沅君在“前言”中阐明她的研究动机——“‘词’是中国诗歌的主要体裁之一。但是在欧洲,词却鲜为人知:据我所知,欧洲既没有词的翻译,也缺乏相关的批评研究。甚至在中国,直至今日,虽然几乎所有的文学院都在教授词,但进行词的系统研究者也是寥寥无几。这就是我开展本项研究的原因所在。”
杜泽逊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我想这是中国学术史和中法学术交流上的重要文献,其意义远不止于冯沅君先生个人学术生平的研究。”冯沅君博士论文的首次出版,不仅解决了学界在研究冯沅君生平学术时的诸多困惑,同时,这篇博士论文本身也是一本简明扼要的通代词史典范之作。文辞通达、论述简洁,不仅适宜专业学者阅读,也适合普通读者作为词学入门读物。
此外,《词的技法和历史》附有五百余条脚注,对涉及的人物、著作、职官、地理等文史知识进行解释说明,其中大多是中国读者习见的常识,例如,把“翰林学士”注释为“类似于法兰西学院院士”,把“赋”注释为“有韵律的散文”,为西方读者构建了独特的跨文化注解体系。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