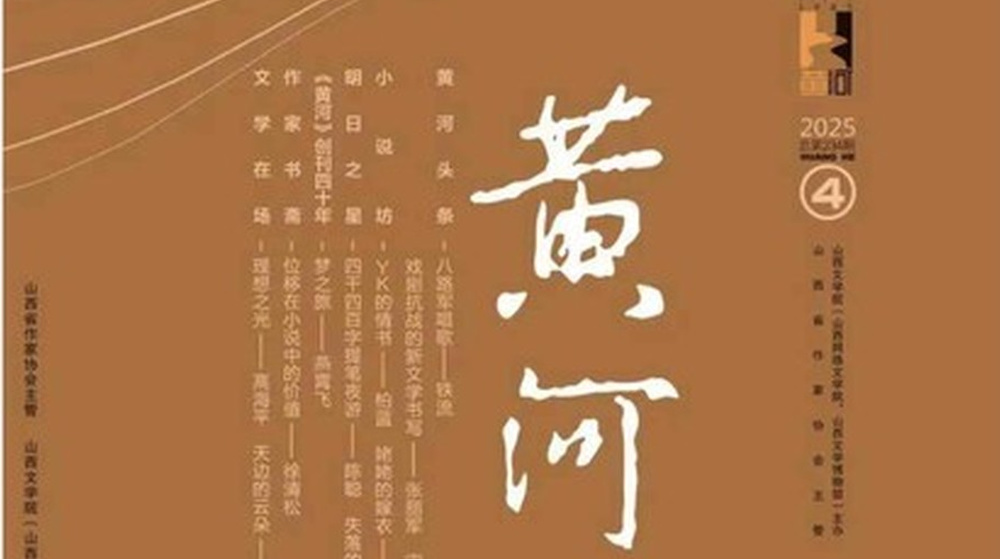日前,著名作家铁流的新作《八路军唱歌》在大型文学期刊《黄河》发表。该作品一经发出,引来了一致好评:《八路军唱歌》是一部“用心”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生机和烟火气”的作品,更是一部有蓬勃生命力的作品。它赓续了现代文学以来的创作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了新的叙事内容,采用了地域风景美学的审美形态,为抗战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审美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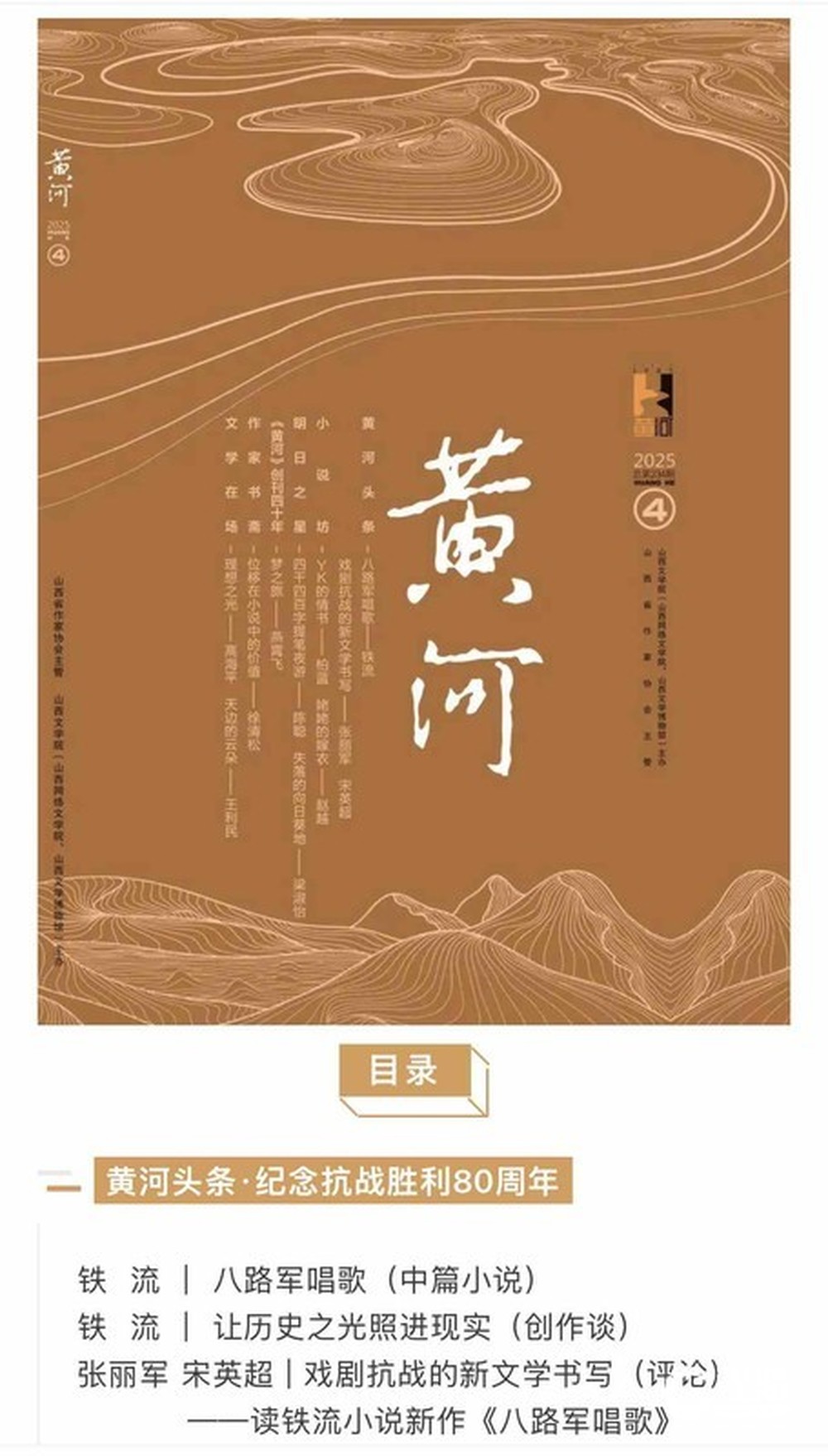
铁流曾说:“文学创作需要用心去触摸,需要用双脚去丈量。足不出户闭门造车,也许你写得很精致,但往往缺少了生机和烟火气。纸花再绚丽,毕竟是没有生命的。”这是他对文学创作理念的阐释。著名文学评论家张丽军表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反映抗日战争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大题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文学作品。《生死场》《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从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根据地生活等不同的角度,近乎全景式地反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历史,构筑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种书写抗战的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并持续产生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学作品。
铁流是一位创作成绩斐然、有影响力的作家。他创作了《靠山》《烈火芳菲》《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等大量反映抗战历史的非虚构作品。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铁流围绕根据地“戏剧抗战”历史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八路军唱歌》可谓正当其时。
《八路军唱歌》在叙事上发掘了以往小说很少表现的新题材、新内容。它主要围绕戏剧抗战这一历史事实展开。小说开头以一首民谣引起叙述,“唱歌”是整部小说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小说反映了沂蒙山地区“姊妹剧团”在敌后根据地开展戏剧表演的故事。
张丽军认为,除了叙事内容的创新,铁流还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开拓。小说的情节相对来说并不复杂。事实上,越是简单的情节就越考验写作者的叙事技巧,否则很有可能使小说流于平庸,损害小说的审美性。在这一点上,铁流并没有简单地处理小说的叙事。他在《八路军唱歌》中通过多元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既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又在情感、细节的“褶皱”中发现了历史的温度。
在当代文学的发轫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曾经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小说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这些作家大多是革命的亲历者,因此他们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回忆录的特点。一方面,小说因此具有了史料般真实的质感,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作者的意识过度介入叙事,也使得小说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较为单调,无法在叙事中灵活地采用多种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表现革命历史的全貌。《八路军唱歌》在题材上属于革命历史小说一脉,但是在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应用上则更加现代。
《八路军唱歌》在见证抗战历史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景美学特征。首先,《八路军唱歌》通过运用多种地域性意象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延宕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丰富了文本的可解读性。其次,铁流在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性方言俚语和生活用语,令整篇小说充溢着浓厚的地域风情和生活气息。《八路军唱歌》将历史性、地域性与审美性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地域风景审美价值。
铁流的新作《八路军唱歌》延续了他以往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将历史镜像与地域风景美学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小说既忠实地记录历史,又在审美性方面突出作为文学作品的特点,对抗战历史进行了新的审美创造性书写。《八路军唱歌》在内容上关注到了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戏剧抗战历史,复活了一段尘封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后人真切地感受到那段风云历史,让生活在革命“第二天”的读者清晰地认识到“全民抗战”的意义。同时,铁流将历史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多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使小说得以深入历史的腠理,表现不同性别、身份的人在抗战中的所感所想。大量方言口语、民谚俚语的运用使整部小说充满地域风情和生活气息。
铁流在《八路军唱歌》中将历史性与艺术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提升了作品的感召力。铁流继承了革命书写的优良传统,又在地域风景美学话语的烛照下实现了新的突破,丰富了新时代红色文学的创作,为红色记忆的赓续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样本。
编辑: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