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下午,广西南宁,装潢精美的漓江书院,涌入了各路媒体、出版机构和市民读者。一摞摞还带着纸香味的新书,被精心摆放在金色的麦穗花束旁边,空中悬挂着巨幅彩色海报,上面印有“将生活淬炼成传奇——《泥潭》刘楚昕新书发布会”的醒目字体。
在优美的钢琴声中,这场活动的主角刘楚昕应邀从人群里现身。宽松的黑色T恤,配上短裤球鞋,好像从大学校园漫步走来的学生。“我没想到今天这么多人,早知道我就穿得正式一点了,还好没有穿拖鞋过来。”面对密密麻麻的听众,他不好意思地调侃自己。
这位在一个多月前还名不见经传的90后写作者,刚刚从余华手里接过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一番真挚的获奖感言,让他意外火爆全网,甚至带火了这个新设立的奖项本身。在公众的热切期盼中,他的作品《泥潭》于6月12日开启线上预售,短短三周就售出40万册。漓江出版社社长梁志在发布会上激动地宣布,这个数字“创造了近年来文学出版的奇迹”。
新书首发仪式后,南都、N视频记者与刘楚昕当面交流。他身上还有未经聚光灯炙烤的朴素,语速偏快,夹杂着文学术语和哲学名词。但细听下来,他对于很多问题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考,或许是因为学习哲学,赋予他更为超脱的视角,或者说“旁观”这个世界的能力。
他自嘲是“流量作家”,出圈的过程是意料之外的,但结果是好的。“我写的这个故事、我创造的这个世界,终于有人注意到了。”
凭《泥潭》走出“泥潭”
5月27日,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刘楚昕哽咽讲述了自己的创作故事和已逝女友的温情鼓励,打动无数网友,新华社、人民日报都转发了他的获奖感言。
但就在流量暴涨之时,刘楚昕选择闭关打磨书稿。5月31日,他通过漓江出版社回应:“此刻我最紧迫的事是回到书桌前,专注文字。谢谢你们对一名平凡写作者的理解和宽容,请允许我暂时沉默。待新书上市时,书页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最诚挚的答复。”
直到7月4日,刘楚昕才带着已经成书的《泥潭》,回归公众视野。新书发布会上,他主动回应了那些最为尖锐的问题。
比如,为何在颁奖典礼上怀念女友,是不是“消费对方”?刘楚昕说,当时没想太多,就是“之前被压抑得太久了,想在公开场合说一下”。
又如,整个事件是不是一次营销炒作?他回答道,其实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因此受到大众关注。“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事件,它的结果是好的,只是它的过程是意料之外的。”当纯文学奖项获得了流量,文学新人有了一夜成名的可能,也会带动更多公众去阅读好的作品。
当然,如果没有一夜成名,刘楚昕依然会按部就班、缓慢而坚定地走这条文学路。

刘楚昕的获奖感言曾打动无数网友
他自认为不是“拥有顶级天赋的作家”。从十三四岁萌生作家梦,之后的十几年一直在写,投稿多次被拒也没有放弃。读博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就算跟女友一起散步的时候,都牵挂着没有写完的作品。
在回答南都记者关于“为何坚持”的提问时,刘楚昕谈道:“可能跟我这个性格有点关系,说难听一点叫偏执,说好听一点叫执着。你说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也很难说。万一我没获这个奖,好像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坏事,就是‘人不应该这么偏执’。”
尽管十几年来都没能发表一篇作品,刘楚昕还是设法为自己找到了努力的刻度。
“到2020年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主流文学期刊的编辑回复了我,认可我的文字水平。这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有进步的。又过了几年,《泥潭》的早期版本入围了一个文学奖,我心里就觉得,这样改是对的。如果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改下去,总有一天我的作品有机会出版。”
2024年10月,第二届漓江文学奖启动征稿。300多份来稿经过两轮评选,共有6部作品进入终评环节,刘楚昕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作者。担任评委会主任的著名作家余华,对《泥潭》青眼有加,最终评委会决定,对它授予本届虚构类奖正奖。34岁的刘楚昕,终于走出了“投稿、退稿、改稿”的循环,第一次触碰到他的文学梦想。
意外获得全网关注之后,刘楚昕保持着反躬自省,乃至于“自我审判”。
他说:“我很不愿意跟人合影,很不愿意帮人签名。因为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一个人的名气如果大于实力,这个人就是华而不实的、虚假的、可笑的。没想到我自己居然变成这样的人了。现在每天感觉我头顶上有眼睛在看着我,跟我自己的‘超我’在看着我一样,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于实力,你现在是一个流量作家’。确实是这样。”
刘楚昕坦言,他会因此感到焦虑,“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是不是?必须要对得起各位评审老师,对得起出版社,对得起读者。那就只能更加努力去改这个稿子,尽我最大的努力。所幸,最后出来的水平还在及格线之上。”
一部“难懂”的作品
《泥潭》是刘楚昕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构思始于2013年。
故事以辛亥革命的序幕武昌起义为背景。回忆当初为何会选这一题材,现在他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非常偶然。“那时就是想写一部有激烈戏剧冲突,以及涵盖形形色色不同阶层人物的‘史诗般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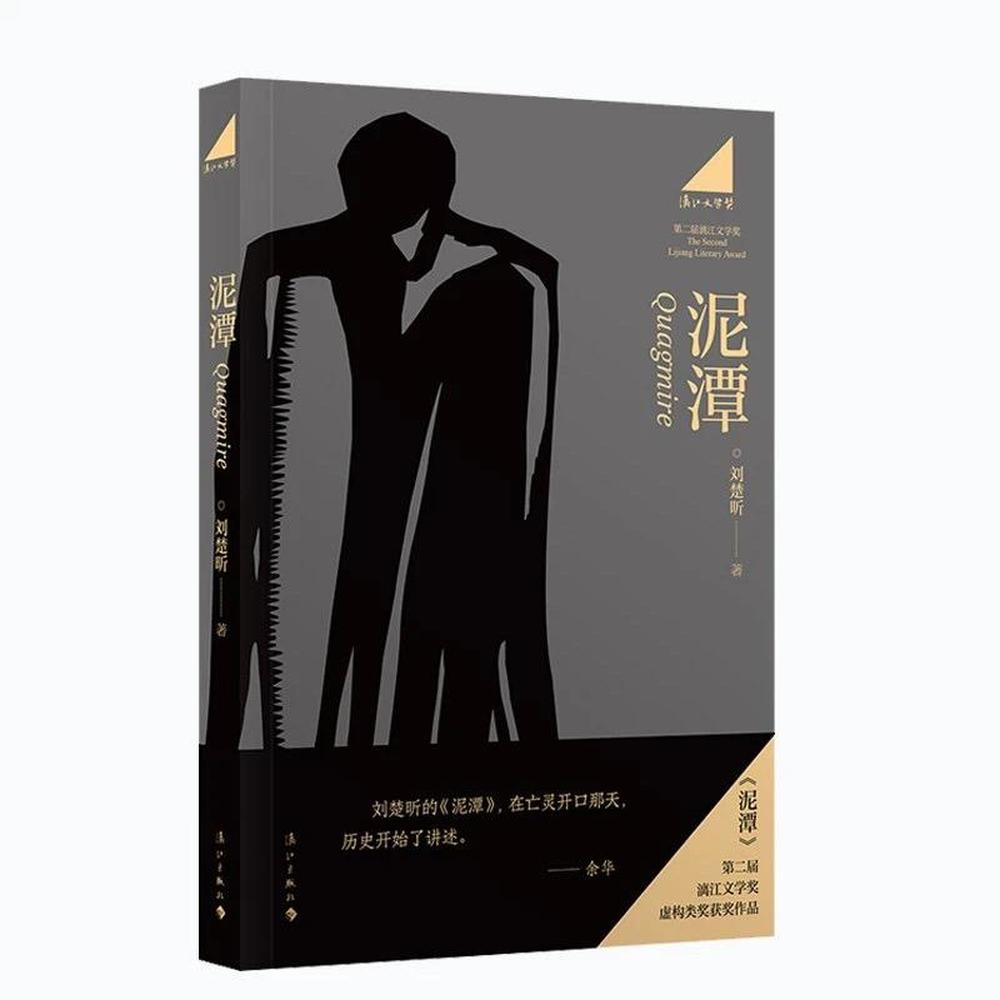
《泥潭》书影
在湖北荆州土生土长的他,曾翻阅老家的地方志,发现清末时期即充满了这样的冲突,于是就动笔了。但他没想到,这部书稿的创作过程会如此漫长、磨人。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文学审美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50万字的初稿经过反复删改,最终定稿只剩下17.4万字。
刘楚昕介绍,小说最后一次大改,受到了两部小说的显著影响。
其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作《喧哗与骚动》,他从中学习了多视角叙述、意识流等现代派的写法技法;其二是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借鉴其“电影般的文字质感”。此外,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影片《日落大道》也给他带来了创作启迪,电影开头即呈现了一个年轻男性的死亡,而后让死者开口叙述。因此,《泥潭》的开篇就是主人公之一恒丰回溯自己被处决的情景:“如您所见,我死了……”就像一部影片的旁白一样。
对读者来说,《泥潭》绝对不是一本易读的书。故事分为三个部分,各有主角但又彼此联系。除了身为湖北没落旗人的恒丰,还聚焦了代表社会新力量的革命党人关仲卿、圣母堂神父马修德等人,时间跨度三十余年。书中出现了真实存在过的宗社党,以及秋瑾、陈天华等历史人物,另有一些角色存在对应的原型,考验着读者对于历史细节的熟稔程度。
小说第一部分采用的非线性叙事叠加意识流手法,更对阅读理解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些段落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不过,在刘楚昕看来,自己还是有一些“照顾读者”的自觉,至少比《喧哗与骚动》容易懂。为了降低难度,他还通过切换字体,留下了“此处有闪回”的明确提示。
从一部文学比赛的投稿,到正式出版的书籍,《泥潭》的编辑出版过程十分紧凑。据此书三位责编之一谢青芸透露,直到付梓之际,刘楚昕仍对书稿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尤其是小说的第二、第三部分,都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刘楚昕在新书发布会上
而刘楚昕坦言,由于写作时间太长,不同时期的文本混杂在一起像是在打架,让他改起来颇为艰难,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无法令自己完全满意。“是我的责编告诉我,世上没有完美的稿子,就到此为止。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说,我和这部小说之间漫长的拉扯终于结束了。”
而他对历史题材的耐心,至此也就消磨殆尽,“绝对不会再碰了”。在他看来,今天的写作应该更关注当下的生活,自己也开始着手写新的草稿。
“如今中国真的是一片文学的沃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极具冲击力的现实。只是需要更多的作者去挖掘这个文学的宝库、写出来。我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
刘楚昕说,“虽然我的实力是怎么样,我心里很清楚,说是‘添砖加瓦’可能都有点自夸了。我就是想试一试,看自己究竟能不能在这个领域上有所突破。”
用哲思俯瞰日常
除了从事文学创作,刘楚昕的另一重身份是哲学研究者,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楚昕的高中班主任、湖北省特级教师周守国告诉南都记者,虽然他在高中阶段读的是理科,但对哲学和文学都有浓厚的兴趣,阅读面相当广,“他喜欢读弗洛伊德、康德等哲学家的书,李泽厚的美学书也爱读。” 高中时期,刘楚昕话不多,爱思考,很有个性,作文有自己的观点,观察问题深刻,但又不偏激。
2008年,刘楚昕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爷爷不想让他报哲学专业,担心不好就业,但周守国鼓励他顺应本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终,刘楚昕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录取,本科毕业后留院读了硕士。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尼采,硕士研究的是魏晋玄学。”刘楚昕介绍。
硕士毕业后,他于2017年考取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跟随导师吴根友研究了四年中国哲学。
吴根友告诉南都记者,刘楚昕在博士阶段选择了先秦思想、道家思想等作为研究方向,是他自身的兴趣所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用一百多页篇幅梳理阴阳五行观念在先秦及汉代思想中的流变,包括其融入天文历法、数术、政治哲学、医学、易学等领域的过程。

刘楚昕在新书发布会上分享创作过程
2024年,刘楚昕通过人才引进渠道,进入湖北省社科院工作。
这样的知识背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独特的映照。实际上,《泥潭》不只讲述历史,更有一种哲学的俯瞰视角。正如第二届漓江文学奖授奖词写到的,小说让双线人物互为镜像,令人性的善恶互为纠缠。有人完成了精神救赎,有人撕开了命运缺口,更多人颠沛流离于生死两难的陌路。
小说最扣人心弦之处,正是对不同人物命运的摹写。离乱年代,天命难测,在黏稠如泥潭的历史中,人们需要直面生存困境,完成自我救赎。
而刘楚昕借小说中的神父马修德之口,向读者传递了自己的信念:“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这段话也被他以亲笔手书的形式,留在了《泥潭》的扉页。
在交流中,南都记者问刘楚昕,如何看待命运?尤其是对个体而言不可预知的厄运?
刘楚昕回答说:“我觉得命运是一个后验的词。我们都处于自己的因果性之中,只有在最后才能回看,何为命运。”至于厄运,他理解为“一次重新看待人生、审视生活的机会”。他谈到,生活中有很多看似平常的东西,失去后才能发现它们有多宝贵;而另一些平时被看得很重的事物,厄运到来之际,人们才意识到,其实它们没有什么意义。
就像巨大流量可能带来的名和利,刘楚昕说,他对此没有什么欲望,看得比较淡。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高贵的东西,总是非常容易消失的。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痛苦,痛苦的时间总是比快乐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正是那些一闪而过的高贵的东西,支撑着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希望他的演讲也好,小说作品也好,能在某个瞬间打动别人,给大家提供一些值得向往的美好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