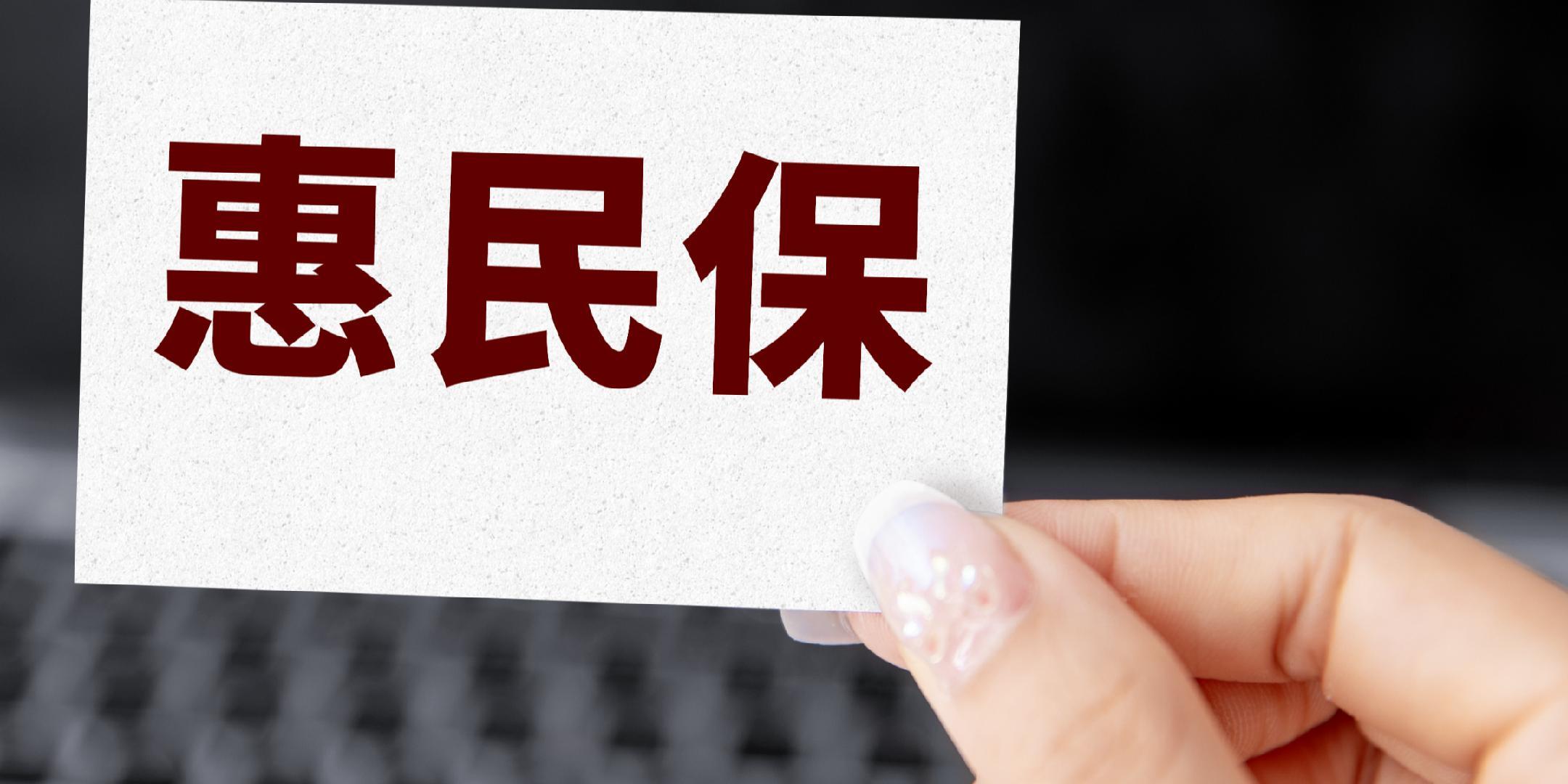停牌500多天后,诺辉健康终于官宣退市。10月22日晚,该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因不能履行复牌指引,停牌超18个月,香港联交所将在10月27日正式取消公司的上市地位。
曾被誉为“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的诺辉健康为虚增检测量,竟然向环卫工人购买公厕粪便作为检测样本来源,更有甚者,将一份样本拆分为多个虚假账户,伪造检测数据,最终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告别资本市场。
2025年IVD(体外诊断)行业正经历供需失衡、竞争加剧与转型阵痛叠加的“寒冬”,“作为港股上市公司,诺辉的快速扩张坠落,折射出了行业发展的痛点,也对整个IVD行业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某IVD从业者向媒体记者表示。
快速崛起
诺辉健康的故事始于2015年,由三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朱叶青、陈一友和吕宁,三人看准高发癌症的早筛市场后,当年联手在杭州创立。
诺辉健康核心产品是结肠癌早筛产品“常卫清”和“噗噗管”,专为中国1.2亿结直肠癌高危人群打造,开启了癌症居家早筛的新篇章。
2020年11月,诺辉健康迎来高光时刻。“常卫清”拿下“早筛第一证”,是国内首个获批的癌症早筛产品,“噗噗管”也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并开始正式商业化。“常卫清”是目前国内唯一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分子癌症筛查测试产品。
朱叶青称,“常卫清”研发时间长达五年,经历了6个月的试验设计、16个月的试验、11个月的注册审批流程,投入资金超过1亿美元。他强调,如果潜在竞争者想要获得同类批文,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此外,公司还拥有三款适用于肝癌、鼻咽癌和宫颈癌筛查的在研产品管线,并联合北大医学部正式启动中国泛癌种早筛早诊队列PANDA研究项目。
2015年—2021年的六年间,包括软银中国资本、君联资本、启明创投、礼来亚洲基金、美国杜克大学资产管理公司、夏尔巴投资等数十家VC/PE、产业资本对诺辉健康进行了7轮投资,总金额超1亿美元,为其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2021年2月,诺辉健康成功登陆港交所,成为“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上市当日市值一度冲破300亿港元,备受资本市场追捧,也为中国癌症早筛行业注入强心针。其股价一度飙升至89.65港元,市值突破400亿港元,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
此间,公司财务数据也光鲜亮丽:2022年营收7.65亿元,同比增长259.5%;2023年上半年营收8.23亿元,已超2022年全年,风头一时无二。公司前董事会主席朱叶青变得“高调”起来,他说,“希望有更多人受益于癌症筛查,改变生命轨迹。”
快速坠落
有没有更多人改变生命轨迹是个未知,但因数据造假,公司的“命运轨迹”被改变了。2023年8月,一个名为CapitalWatch的账号发布了一篇《关于诺辉健康财务数据造假的调查报告》,指责公司2022年销售数据不实,“实际销售额可能仅为7695万元人民币,与其公布的7.65亿元相差近9倍”。报告还质疑其检测样本真实性,暗示存在系统性造假行为。
更令人咂舌的是,2025年10月有媒体爆料,为虚增检测量,诺辉健康曾向环卫工人购买公厕粪便,作为检测样本来源;甚至还将一份样本拆分为多个虚假账户,伪造检测数据,涉嫌严重违反医疗伦理。
起初,诺辉健康否认指控,朱叶青跳出来给公司站台“打嘴仗”,却未提供具体证据“自辩”。由于长期发不出财报,公司市值一路暴跌至63.45亿港元,被迫停牌,超336亿港元灰飞烟灭。
面对质疑,诺辉健康管理层曾强硬回应,强调“收入合规、审计严格”。但2024年3月27日,其长期合作的审计机构德勤突然“跳反”,拒绝为2023年财报背书,并发出关注函,直指销售数据真实性存疑。
2024年3月28日,港交所强制诺辉健康停牌,股价定格在14.14港元,较26.66港元的发行价已近腰斩。紧接着,公司创始人及高管团队开始分崩离析,2024年9月,公司CFO高煜等高管接连离职,2024年12月30日,诺辉健康创始人朱叶青被罢免执行董事及其他所有职务。
按照港交所的规定,主板上市公司连续停牌18个月,可取消其上市地位。10月22日晚,诺辉健康发布公告称,因未能于2025年9月27日前履行复牌指引,港交所上市委员会已决定于2025年10月27日上午9时起取消其在交易所的上市地位。
IVD行业启示
目前,诺辉健康已进入临时清盘程序,董事会权力被全面暂停。其投资者损失惨重:光证资管对其估值已下调至0.01港元,几乎“归零”。 从“早筛先锋”到“粪便造假”主角,诺辉健康的覆灭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失败,更是中国医疗资本狂潮中一次深刻的信仰崩塌。
诺辉事件把IVD行业最脆弱的三个问题暴露出来。一是支付方缺位:C端烧钱补贴不可持续,企业为了维持股价和市值,采取财务造假手段。二是临床价值未被充分验证:产品过早被资本催熟,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预期,虚增收入和销售额。三是众多VC对“非血液类早筛”列入“红灯赛道”,原则上暂停新投。
分析认为,2025年上半年,IVD行业已经“举步维艰”,标志性事件是,龙头企业迪瑞医疗上市11年来首次半年度亏损。回溯2024年,行业颓势已现:迪瑞医疗全年营收同比下降11.63%,净利润同比下跌48.5%至1.42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从2.24亿元逆转为-2.95亿元,同比降幅达231.29%。
迪瑞医疗的业绩滑坡并非个例,而是行业整体承压的缩影,在多数本土IVD企业中具有普遍性。2025年IVD行业正经历供需失衡、竞争加剧与转型阵痛叠加的“寒冬”,头部企业首现亏损,中小玩家生存压力陡增。分析称,产品结构失衡、内外竞争挤压、政策与资本退潮,扩张泡沫破裂让IVD“寒冬”持续。
尤其是资本退潮,对IVD行业打击沉重。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IVD私募融资仅完成18起,同比断崖式下滑超40%,陷入“量价齐跌”的冰冻期,并购市场同样冷清,数量锐减,大多数企业缺乏输血渠道。
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研究的奥优国际董事长张玥认为,诺辉健康从“癌症早筛第一股”到退市,反映出高增长叙事下的共性风险,包括过度依赖资本输血、商业化进程缓慢、市场实际需求未被充分验证等。“这些风险在生物科技领域较为常见,企业往往在技术未成熟时就急于上市融资,导致后续发展乏力。”张玥说,“未来,资本会更加倾向于投资技术成熟、商业化路径清晰的企业,行业可能进入理性调整期,促使企业注重产品实效而非单纯追求市场扩张。”
诺辉事件还映射出了IVD行业痛点:一是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癌症早筛产品现阶段没有发挥投保中的控费作用,主要是缺少真实世界的数据积累,企业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二是监管认证与市场渗透难度大:早筛的推广极度依赖认知、信任与渠道及KOL,企业必须投入大量教育成本,这部分支出很多企业无力摊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