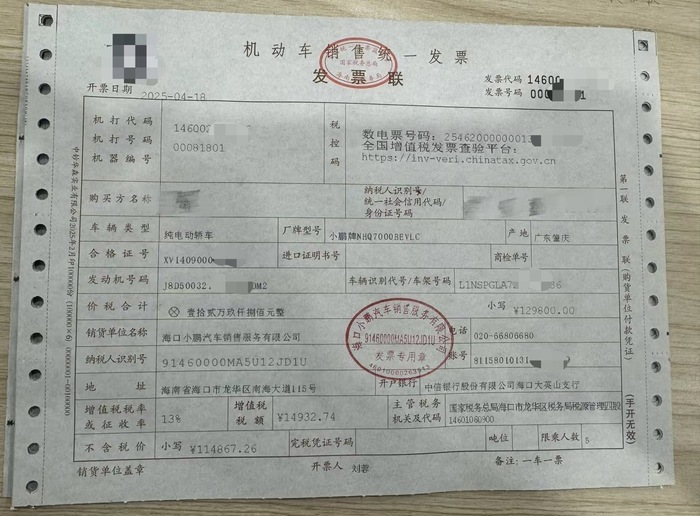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任晓斐
在文学里,“没有县城,万万不能”,如今这股“县城文学热”弥漫社交平台和影视作品,从“鹤岗化”的房子包围北上广深,到《春色寄情人》《微暗之火》《走走停停》里的小镇青年当上主角,县城缘何成了当下年轻人的“精神故乡”?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可以是一种摄影风格
“县城文学”最初是作为一种摄影风格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走红。照片里的主角,充满年代感的打扮,犹如戴望舒笔下的结着愁怨的表情,再配上略带伤感的背景乐,汇成了一种新的摄影风格。
前段时间,济南的一位摄影老师贾小珂也发过不少“县城文学”风格的摄影作品。他表示,“4月底、5月初的时候,一个叫‘乌鸦jewey’的摄影师带他的学员共同创作了一些作品,后来又有几个学员发布后,这种县城文学的风格在互联网爆火。”贾小珂补充说,“其实之前也有过几次火爆,但这次是最火的一次,大家都开始模仿。”
在小红书搜索“济南县城文学”会出现不少摄影作品,照片里的人物让人一秒穿越回千禧年前后。破旧的楼梯、斑驳的木门、年久失修的楼房、老式的自行车、杂乱的电线,以及装修风格数十年如一日的店铺都是绝佳的拍摄背景。
贾小珂说,如果在济南拍摄“县城文学”,他会推荐槐荫区、市中区、天桥区的几个地点,比如经三路、宝华街、南辛庄街道、龙泉商城等。拍摄用的服装道具是贾小珂从各处淘来的,“服装的话,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花衬衫、格子衬衣、牛仔裤、邮差包为主,男士的话会选西装衬衣。”至于妆造,贾小珂说化素颜最好,淡妆也可以,女士可以扎麻花辫,“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化浓妆的不多。”
 《春色寄情人》
《春色寄情人》
哪些人群会青睐这种怀旧的摄影风格呢?贾小珂分析大概有两类人群,“一类是0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格,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喜欢拍民国和古装一样,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想通过拍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另一类是80后、90后会喜欢这种风格,算是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回眸、怀旧。”
不过“县城文学”这种摄影风格来得快,去得也快,在记者找到贾小珂的时候,他说“已经过时了”,“大概火了一个多月吧,从暑假开始,大家就又开始拍旅行照片、大江大河等风景打卡照了。”对于这一风格以后还有无再火的可能,贾小珂认为,“同样的风格应该不会再火,县城风格或许会通过其他场景或妆造再火一把。”
也可以是音乐、影视
去年以来,演出市场下沉到县级城市,“县城文学”的缩影,也从平面摄影作品中铺展到音乐、影视等领域。
《新说唱2024》捧红了一位叫“河南说唱之神”的95后新生代rapper(说唱歌手),他带着自己创作的《工厂》像游吟诗人般将故事娓娓道来,大张伟称他是“说唱界张楚”,也有不少人表示“不知所云”。
“河南说唱之神”本名张方钊,是一个从河南走出的小镇青年。《工厂》走红时,恰巧也是“县城文学”当红的时期,很多有着和张方钊类似经历的年轻人,在他的歌词中寻找触动,犹如那句“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在一种对县城和它所代表的乡愁的复杂情绪中,《工厂》出圈,MV在B站的播放量超过700万。
为县城写歌的还有“五条人”,在他们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县城记》中,单是写海丰的歌就有十几首。在2009年,他们曾在《南方周末》的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这个奖)不是颁给《县城记》这张专辑,而是指向活在大城市、小县城里的每一个平常人。”伴随着十多年后他们登上《乐队的夏天》被更多人熟知,他们的过去和曾经的“县城音乐”也重新被人挖掘。
 张方钊
张方钊
“县城文学”走红在短视频,也深入到热门影视。说起“县城美学”,很多人都要考古到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等作品,不久前,贾樟柯带着他最新的“汾阳故事”勇闯戛纳,在他的影像世界,“县城美学”从未落伍。而放眼今年的多部热门剧集,有多部作品的故事背景都从国际大都市退回了曾经被视为“小地方”的县城。
《微暗之火》讲述了千禧年前后的一座封闭小镇里,一起杀夫案引出了一段注定坎坷的爱情、熟人社会里的善和恶,以及更为复杂的人性。《微暗之火》为婺源文旅又添了一把火,汪口景区的俞氏祠堂和水域,篁岭镇错落有致的房子,秋口镇的油菜花地……这些遍布婺源不同乡镇、景区的画面,共同构成了剧中的“清水镇”。
而另一部讲述青年人返乡的爱情剧《春色寄情人》,也把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放在了县城。女主角从小城走出后,成了上海的白领丽人,在回家的高铁上,遇到了学生时代喜欢的男生,而这个男生也是从外地返乡,如今是当地很有名气的遗体整容师。剧中展现了成年人的爱情拉扯和相互救赎,观众在“磕糖”的同时,也被剧中小城的烟火气所感染。
 《春色寄情人》
《春色寄情人》
在《另一种蓝》里,县城则是都市失意人的避风港。女主角陈小满在北京工作四年,最终选择回到景德镇,捡起小时候热爱的制瓷工作,在家乡原地创业。在这里,县城成了温情、治愈的代表。
就连胡歌、高圆圆也投身“县城影视”,两人的新作品《走走停停》讲述的是一个在大城市受挫的青年回到故乡重启人生的故事。在大城市卷不动,回到小城又躺不平,他被迫陷入走走停停的状态,试着重建生活秩序。
不过,县城不只有回不去的风景,也不只是温暖治愈的底色,还暴露出很多扔不掉的旧习。《微暗之火》里长得好看的女性不仅会被男人惦记,还会被人施加言语暴力。《春色寄情人》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对残疾女主角和和气气。故事的最后,女主角没有选择为爱放弃上海,但也开始习得一份和故乡相处的能力。
“县城影视”的走红不是偶然。《隐秘的角落》带火了拍摄地湛江,《八角亭谜雾》捧红了绍兴,《县委大院》热播后引发了“寻找原型”的热潮,如今再看,从小众到大众,影视取景所引发的文旅热早已为今天的“县城文学热”埋下伏笔。
 《另一种蓝》
《另一种蓝》
还是剪不断的“电子乡愁”
当情绪成为社会热词,躺平、摆烂、怀旧,集体发疯、淡人崛起……年轻人们花式表述着自己的情绪,在“县城文学”走红的背后,埋藏着一代青年的时代情绪和人生抉择,变成一种可看、可听、可感的“电子乡愁”。
作家阿乙在访谈里有过一段关于县城的对话,他表示离开县城最大的原因,是在那儿买不到文学书,如果要获取更多的东西,在县城里肯定不行,这种情况下只有离开。后来他到了北京,才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东西。如今,那些崇尚“县城文学”的年轻人,或者正在老去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和阿乙类似的经历,曾经和县城格格不入的文艺青年,成了如今这个时代的“精神流亡者”。
县城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段时光。“县城文学”的走红是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但在记录和传播的过程中,一些刻板的县城形象开始蔓延,文化现象是情怀使然,却因外界的浮躁而背离初衷。眼下正在大量上市的“县城影视”作品试图探讨一代青年在时代与社会的巨浪中如何掌控好自己的船帆,镜头里的县城有民风淳朴也有居心叵测,有山水田园也有残垣断壁。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县城文学”,在时代情绪的裹挟下,县城不再是一个文化注脚,也不是文艺作品的背景板,只有那些真正脚踏实地在生活中汲取营养的作者,深深植根于地方文化和生活体验的作品才能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校对:冬平 编辑:邢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