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一辆车,满载着一个特殊家庭,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云和月。“人活着大部分时间都是走一条已知的路,反反复复走。”驶过人生的长路,便成山水。
近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著名作家路内长篇小说《山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司机路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五十载的生死相守为主线,辅线铺展收养五个孩子温情与欢笑交织的往事,以一个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欢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的变迁,见证着个体命运与时代史诗的磅礴共振。
路内表示,小说主人公路承宗身上有其祖父的影子。其祖父是一名司机,曾经主动报名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驾驶车辆。从小听说的这些故事构成了《山水》的基本素材。不过,《山水》并不是一部通俗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在小说人物铺展、结构安排上,路内做出了一些融合家族故事与公路小说等元素的尝试。
“我是驾驶员,向来听得多,讲得少。上了我车的人,我不问因果,不问对错。”
“这一世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全办完?”
“一辈子,找条回家的路,走很久,看见自己站在前面。”
这是路内五十岁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简单总结这部小说写了什么,作家的答案是:世道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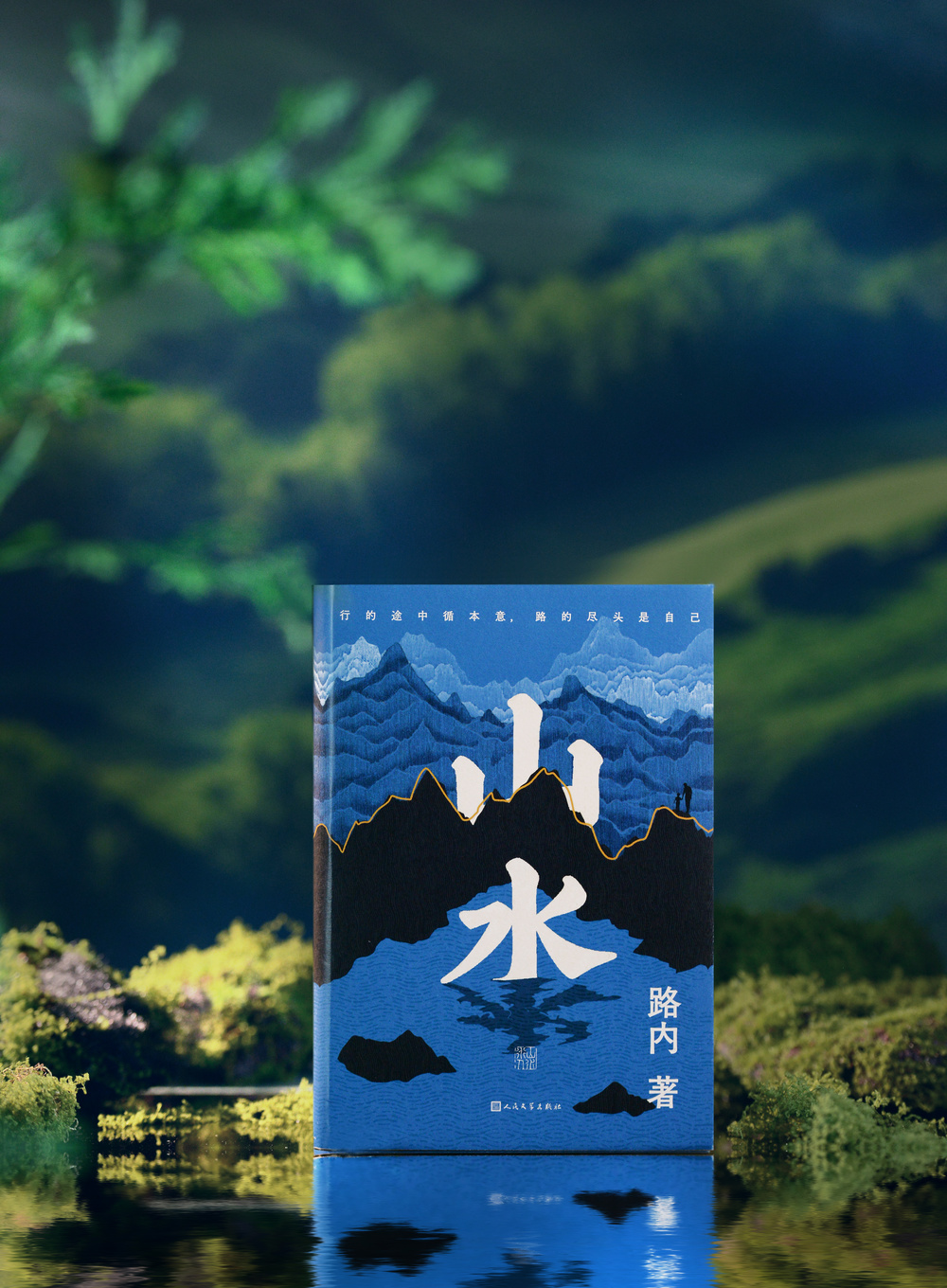
“看山水”是一种人生态度
记者:初看这部小说的篇名《山水》,感觉这个篇名宏大而抽象,也富有多重解读空间;读完小说却又感觉每个人的人生确实行经了无数“山水”。请谈一下缘何以“山水”命名这部小说,以及内封上熊猫意象的含义。
路内:山水其实是一个中国式的概念,早期欧洲翻译中国艺术品,对“山水画”这个品类没有对应词,就直译成了sansui,很显然是南方口音。很多作品确实会找一些大概念,但也有小化的,比如《王子复仇记》听上去很劲爆,实际上是《哈姆雷特》。所以我也不知道,山水这个题目是大还是小,我希望它稍稍大一点,能够越过小说中那些普通人的生活范围,但最好也不要太大。
“山水”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生路,起起伏伏的,山不转水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山重水复疑无路等等。二是在小说里特别谈到了,“看山水”是一种态度,既是胸怀远大,也是隐忍克制。
内封上的熊猫得多说一句。小说结尾写到20世纪90年代,城里有一只来展览的熊猫逃走了,一群人去找。这事还不是我编派的,是真的,那只熊猫不但从动物园逃走,后来回到卧龙山基地又逃走了一次,过了几年又主动回去了。是个好熊猫,生了好几个崽。编辑很喜欢这个故事,他想把熊猫放在封面上,我没答应,有点过分了,但是为了满足他的趣味就放在内封吧。出书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得满足编辑的要求。到底什么意思呢,可能他希望自己是个快乐的熊猫,被大家重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记者:读小说第一章,兄妹五人和路承宗接连出现,会以为是各种线索交织前进的网状叙事,继续往下读才知晓是“打破传统公路叙事的线性模式,创造出一种更为回环往复的叙事结构”。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上,是一种怎么样的考量?
路内:直线叙事很像连载小说,但一个长达六十年的故事,人物众多,要这么写的话我恐怕会堆砌到五十万字去,我感觉太长了,而且无效。小说的主题是人物,还有汽车,并与其相关联的命运。往复的结构可以使故事更凝结一些,在每一章的区间内,有时是一两天之内发生的事,牵涉到回忆,有时是三五年的跨度。这样的写法是否成立,也是一种尝试,尽管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小说,我私心还是希望能给出一个新的文本范式,并且故事能好看些,也不要瞎编。

作家路内
杂糅各种元素的“非家族小说”
记者:在中国现代当小说创作中,或者再往前追溯到《红楼梦》,“家族小说”可谓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样,不仅数量多且姿态万千。请通过《山水》谈谈您创作家族小说的具体实践,以及这类小说如何开拓出新的写作境界?
路内:严格来说《山水》不是一本家族小说,不是《红楼梦》式的。这种小说是横向铺开的,把大家族的细节和人际写得特别饱满。但这类家族在中国基本已经消失,除非是架空写法,现实题材很难再去实现。另一种家族小说是纵向讲述家族脉络的,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一种主流题材,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世界迷宫三部曲》就是典范。纵向脉络的书写又可以产生出变体,比如写一个行业,那就不再是家族小说了。
《山水》取了一个中位线(我自己这么认为),一个没有族谱的大家庭,五个领养来的儿女,一份可以传承的手艺或职业。它具备一些家族元素,或者公路小说的元素,其中也有一些民间元素,比如日本兵进城时关帝庙显灵,很普遍,中国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传说。也许善于糅杂元素能试验出新的路径,把故事讲好。
记者:接着上一个问题,很多家族小说中均有一个“大家长”的形象,《山水》中的这个“大家长”是路承宗。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您的爷爷。请问,路承宗的形象在爷爷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哪些艺术加工?以及这样的“大家长”式的人物,在家族小说中的角色作用?
路内:路承宗这个人物的部分故事取材于我祖父,但具体差异还是很大。小说人物更像我认识的其他人的一种合体。它并非农业或官宦框架下的“大家长”,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人阶层——职业司机在早期也算是技术工种,并且很尖端,有点像现在的程序员吧?这个人物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小时候听镇上的开明绅士讲过一些道理,从业以后听师傅讲道理,打仗了听长官讲道理,他的老婆也是个懂道理的人。价值观是在人生路上习得的,到中年以后他也变成一个讲道理的人。司机是一门必须特别遵守秩序的职业,这种秩序感会让他带有“大家长”的特点,但也非儒非墨,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江湖帮会,更像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大家长在小说中,通常是一个标杆,带有象征性。比如贾政,故事情节上是用来为难贾宝玉的,又比如贾母,是用来调度全场戏的。一般来说不宜作为主人公出现。《山水》这部小说中,路承宗大部分时候是公路小说的格式,小说写了六十年,最后有一点家长气,我认为也是人之常情。我自己祖父就这样,有资历的老司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地位很高。
记者:您觉得,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一个家族故事与时代变迁关系的契合点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家族叙事融入到历史背景中,而不至于显得很刻意为之?
路内:小说家和编剧都能轻松找到你说的契合点,但找到是一回事,写出来是另一回事,写是最艰难的。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故事素材,当然有一些运气成分,如何处理题材又是一门专业技能,和作家风格也有关系。有些作家是反着来的,解构题材,更多地纳入作者审美,有些作家更为中立客观,方法很多,都可以写得很好。比较重要的一条是对历史有认知(解构式的写作可能认知会更深),同时又能具备一种小说趣味,能很好地运行文字。会叙事的作者总能避免刻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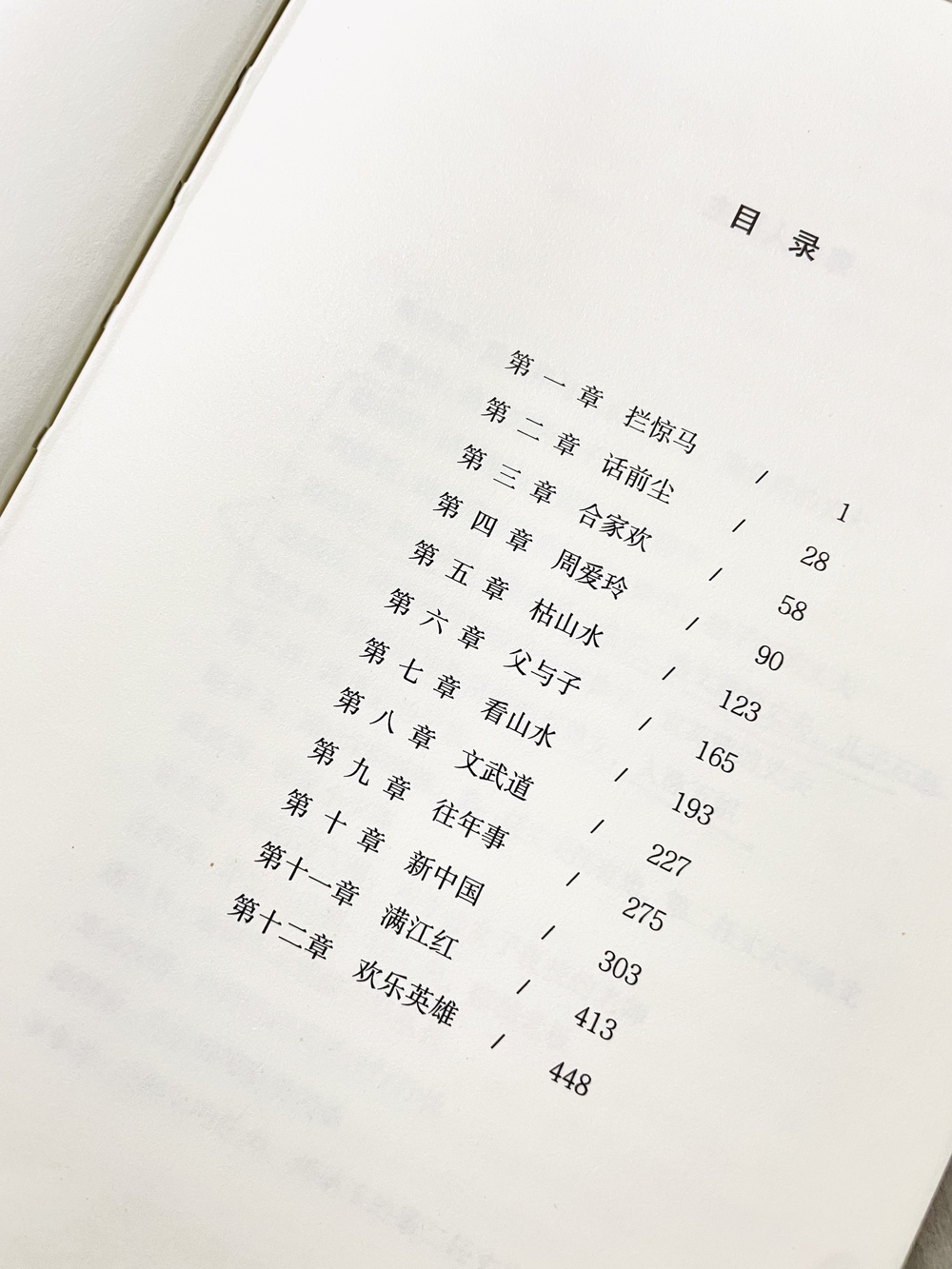
写长篇小说有“模糊的规划感”
记者:有评论家表示,《山水》是您创作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与飞跃,您的创作从“青春叙事”转而更加深沉地回望历史。您自己如何看待这种转变?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规划吗?
路内:早十年前写《慈悲》这本书时就被这么说过一次,后来出版一本很长的《雾行者》,也被说过一次。上一本书《关于告别的一切》没被这么说过,那题材是写一个潦倒中年人回望自己前半生的各种爱情,爱情一旦多了,就显得轻薄,没有深沉感,可它也构成了一种人生叙事。这方面好像大家就比较排斥,至少要显得对此陌生。现在要是有人问我怎么看待爱情,我也会说,哎呀,这个复杂问题我不懂啊,还是谈谈历史吧。这是开玩笑的话了。
新作能被评价为飞跃,我当然很高兴,但自己不应该用太褒义的词去理解问题,假如下一本书仍然写爱情,希望大家不要说我坠落。我这个人一把年纪还是有偶像包袱,听见差评会难过。
《山水》这本书是五十岁以后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对于过往年代那些人经历的事,确实心有戚戚,现在的说法叫共情。你说的自觉度,可能就呈现在这里。写长篇小说有一种比较模糊的规划感,确实是有既定路径,也没有具体到必须奔着某个目标去。就像看足球,观众眼里是一场完整的比赛,但对具体某个位置的球员来说,场上的时间是破碎的,结局是非常不确定的。
记者:请谈一下这部小说过程中您记忆最深刻或者最受触动的一个场景。
路内:有这么一个事情,被写进了小说里,是我外公告诉我的。他说在淞沪会战夜战时,中日双方在战壕里摸黑白刃战。两军绞杀在一起,那种时候如何分辨敌我,不是靠喊话,喊话就暴露了。双方是伸手去摸,摸到布帽子是中国士兵,摸到钢盔是日本鬼子,辨出是敌人就一刀捅过去。杀一夜,天亮后战壕里全是搂在一起互相捅死的人。战争是残忍的,抗战得来胜利也是不易的。
记者:最后,请用几个关键词来向读者推荐一下《山水》。
路内:谢谢,给我自荐的机会。就一个成语:世道人心。
编辑:任晓斐 校对:汤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