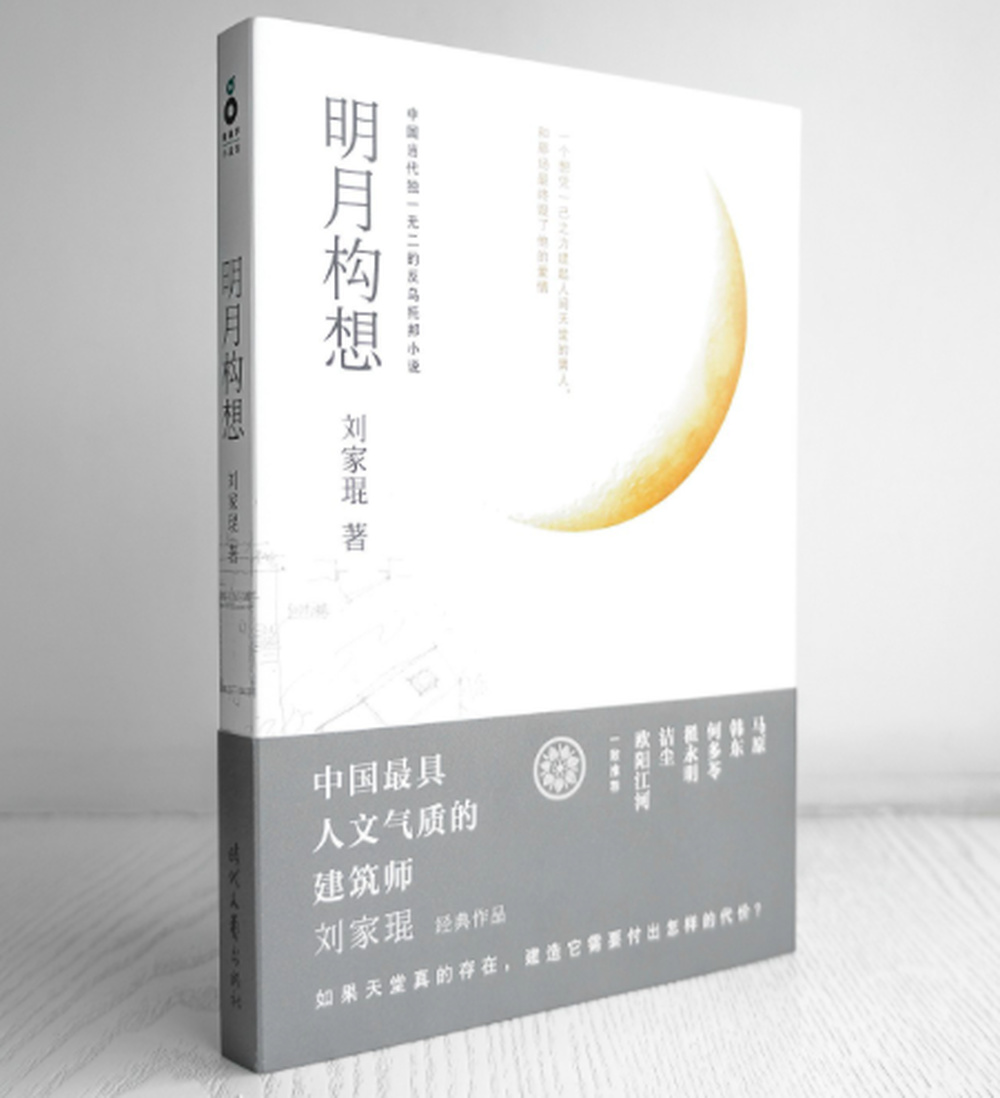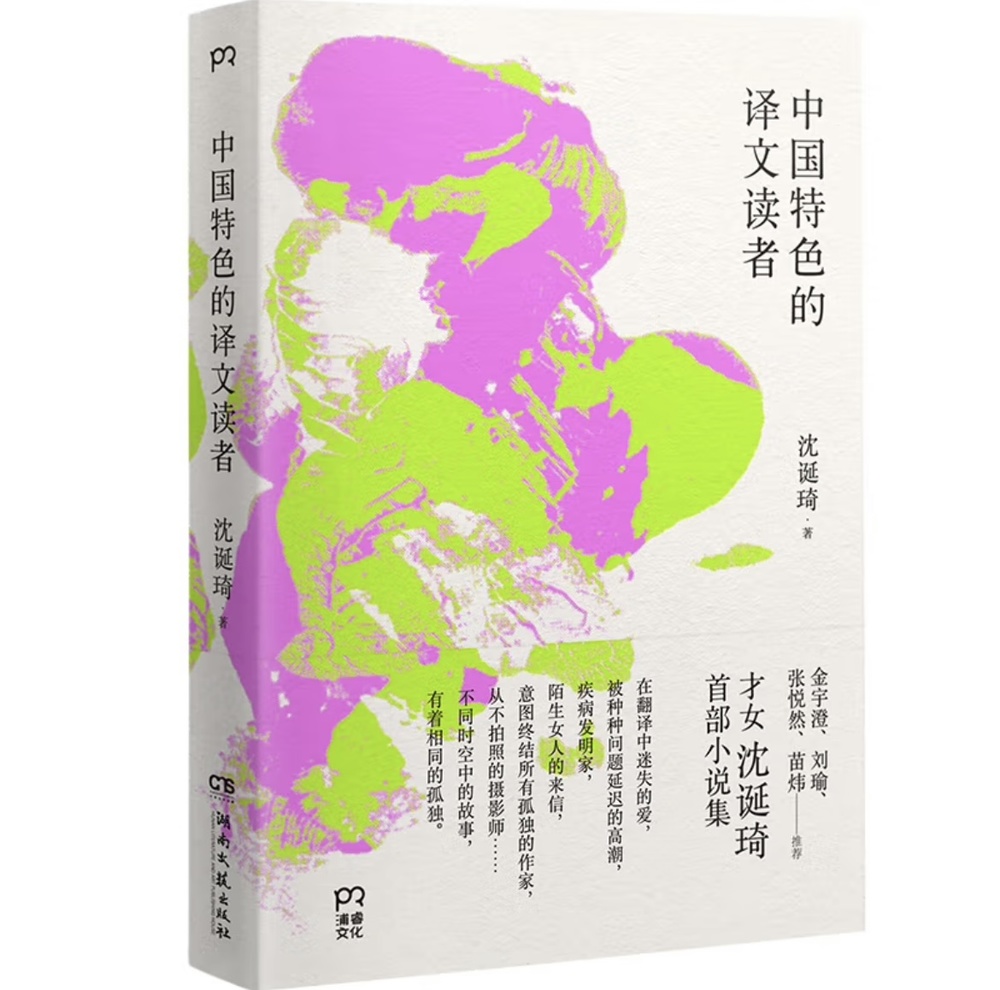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徐敏
贴近大地、富有哲思的散文书写
“我只是耐心地守候过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在永无停息的生命喧哗中,我看到因为死了一只小虫而从此沉寂的这片土地。别的虫子在叫。别的鸟在飞。大地一片片明媚复苏时,在一只小虫子的全部感知里,大地暗淡下去。”
作家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只需这短短一段话,读者就可以感受到刘亮程散文的从容、平和、哲思以及自然气象。因其独具风格的散文创作,刘亮程也因此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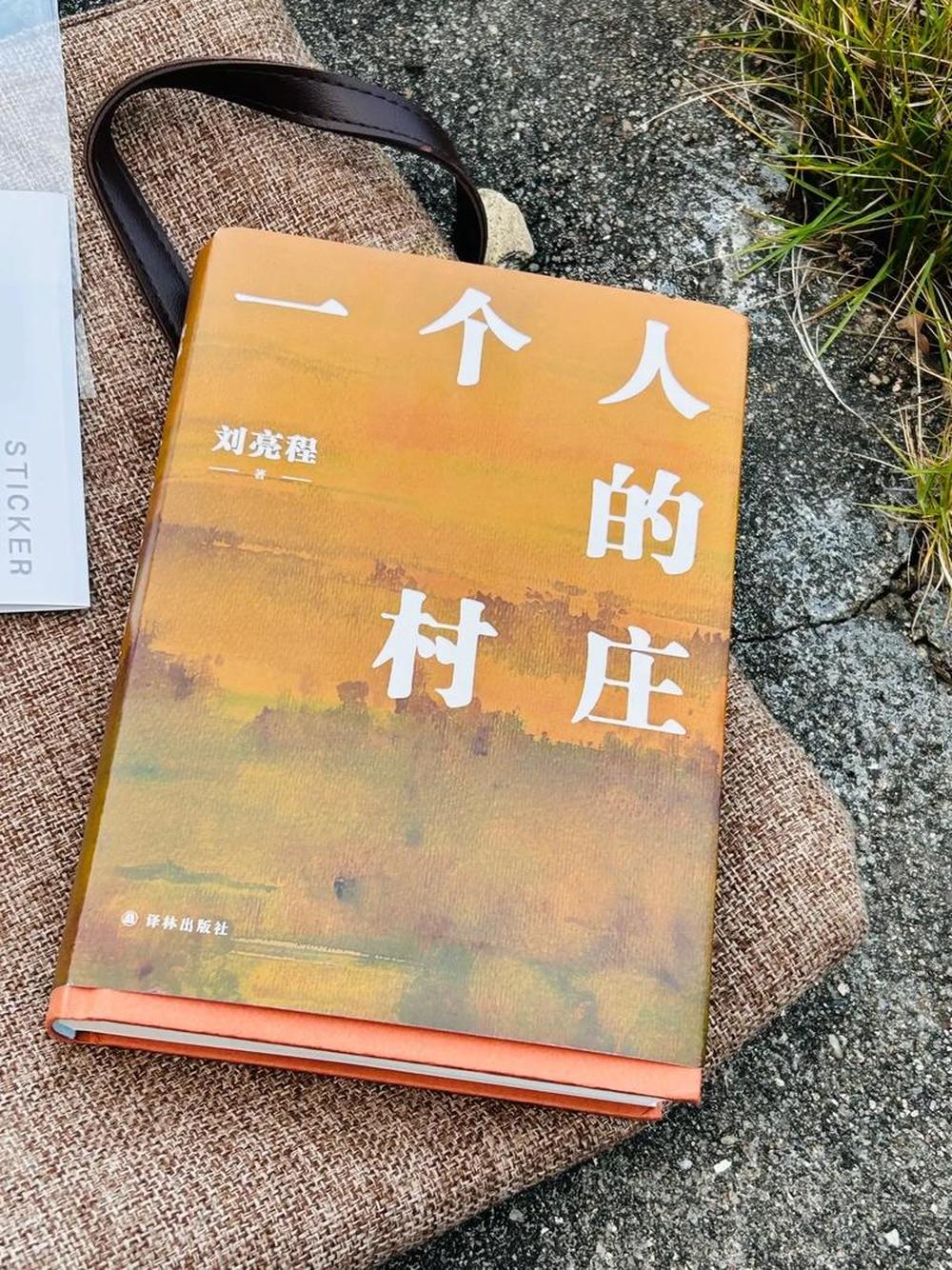
散文如何写?鲁迅先生说,是大可以随意的。散文评论家王兆胜说,21世纪之前,学界一度倡导“人的文学”,作家注重塑造典型人物;21世纪之后,许多散文家全力以赴写“物”,努力展现“物性”的光辉,在万物描写上倾注心力的生态散文快速崛起。通俗来说,如刘亮程这样的散文作家观照的是自然万物,根植于乡村生活的日常,贴近脚下的大地,用爱和慈悲的眼光深情地观察世界的一草一木,从而给出关于生命的哲思。
如此,刘亮程的散文给读者非常不同一般的阅读感受——他明明书写的是鸡鸣犬吠的村庄,却能超越凡俗的烟火气传达出独特的生命哲学。敏感的作家能听懂万事万物的呼唤,并且把这种交流和感知融化于文字之中。村庄里的人、牛、马、狗,大树、房屋、鸟巢,村庄上空的天空、白云,村民脚下踩踏的土地,甚至是这座村庄呼吸出的空气,都在作家笔下反复交织出现。而让作家将这些乡土元素浑融地编织到文字之中的,则是他充满意识流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刘亮程呈现的村庄、自然和世界,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灵的。
同样书写新疆风物,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与刘亮程相比,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她笔下的大梁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村庄,烟火气十足:“你家种豇豆,他家种茄子,我家种辣子,谁家的先成熟了就摘一些下锅,你今天摘我的辣子,明天我摘你的茄子,一家种一样东西,十几家的菜合在一起,就能做出一桌像样的菜来了。”读帕蒂古丽的散文,眼前浮现的是无论幸福或者贫瘠,但是都热气腾腾的生活。
从作家的理念中可以追溯到这种文风的差异。刘亮程认为:“散文是一种飞翔的艺术,它承载大地之重,携尘带土朝天飞翔。”而很多作家是“爬行动物”,低着头写作,“他们从来都不会走一会儿神。”
近两年,另一名书写新疆的作家受到关注,即《我的阿勒泰》的作者李娟。李娟的散文书写新疆的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地的生活图景。她的文字中也有对生命的感悟,不过并非刘亮程式的哲学化沉淀,她的角色是生活的亲历者和记忆的收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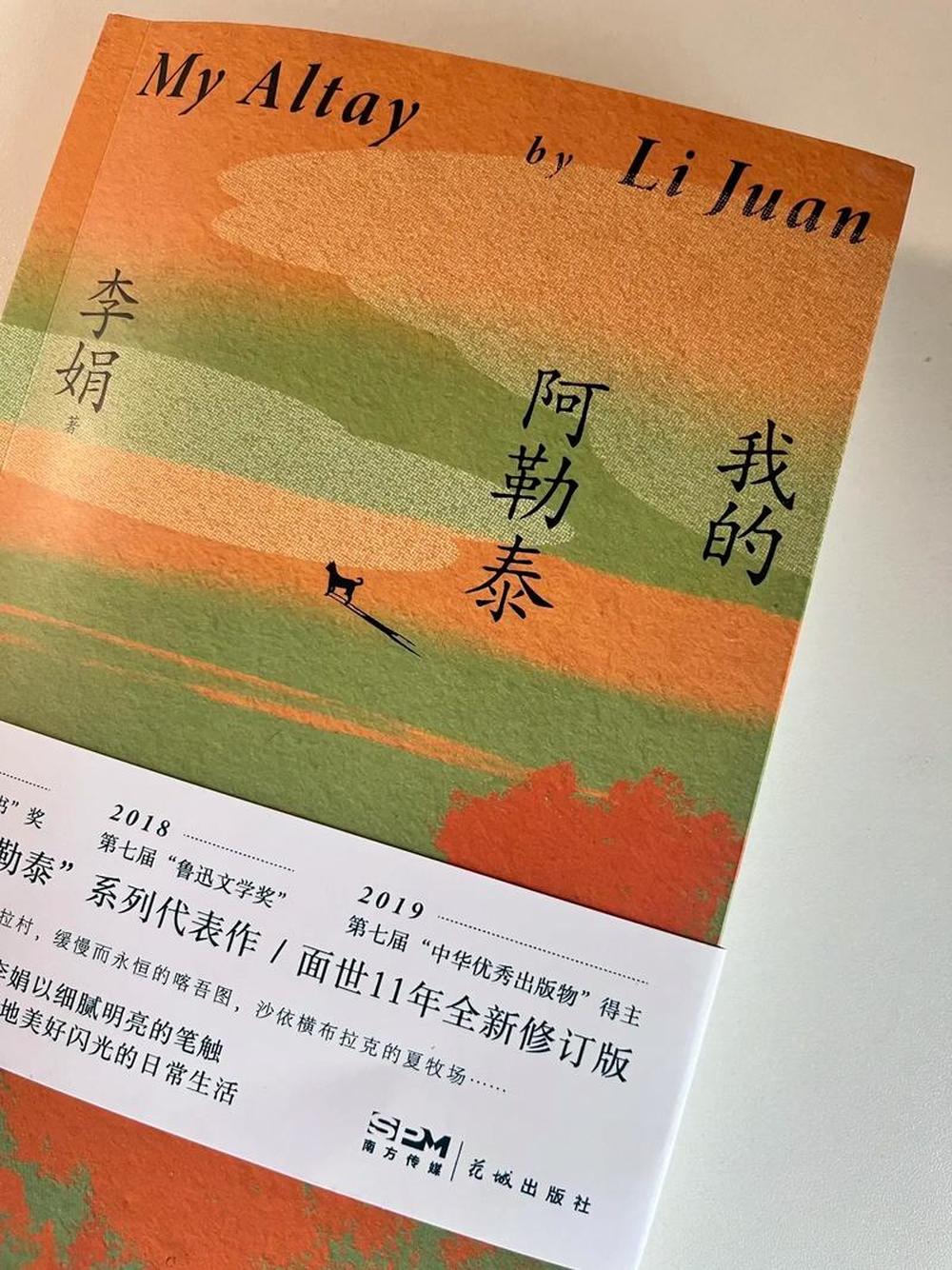
散文作者是“大自然的布道者”
散文家傅菲,是继刘亮程之后迅速崛起的散文家。傅菲也是一名自然散文的写作者,他的作品中对山川草木植物动物的关注与表达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如评论家张守仁所言,他观察风霜雨雪,细看鸟巢蚁穴,注视树叶间泄露的光线,听听布谷蝉鸣,闻闻溪水潺潺,喜见所栽秧苗渐渐长大。最终,傅菲在他的散文世界中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伦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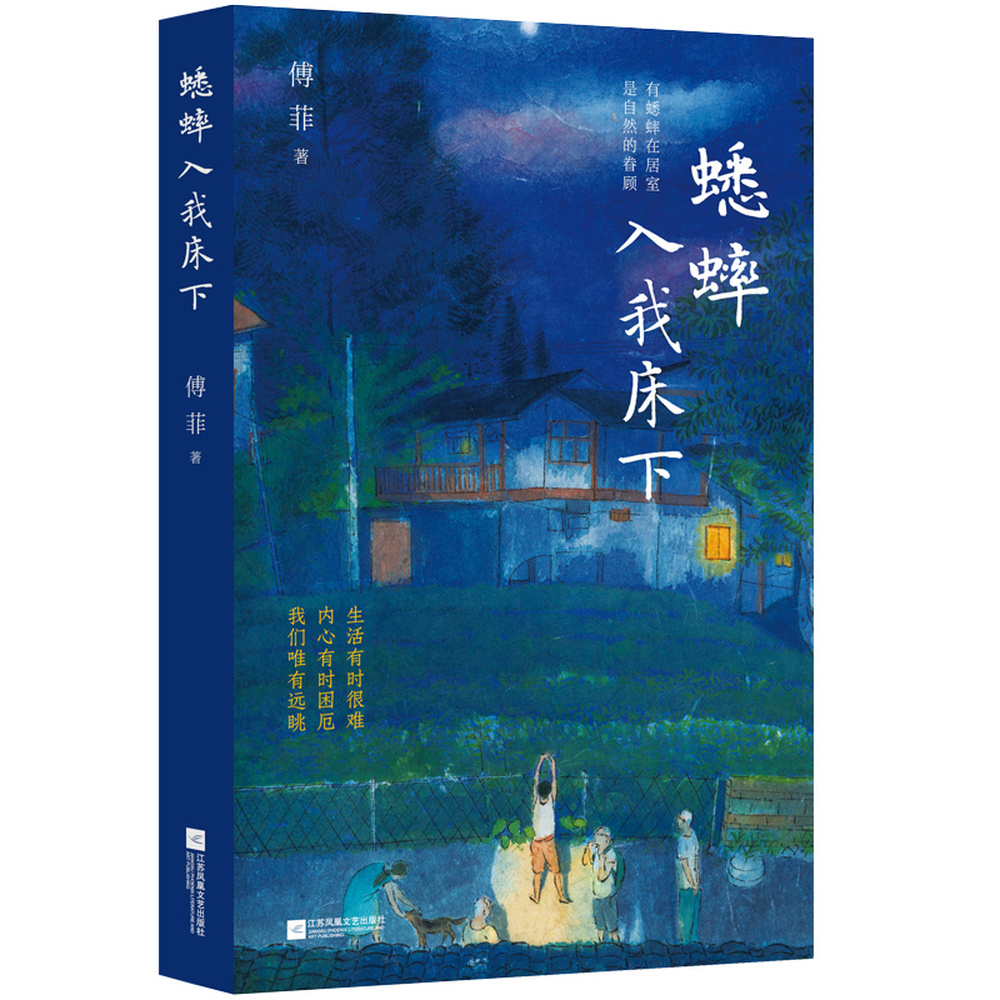
傅菲的这种书写与刘亮程又是不同的。刘亮程让文字飞翔起来,充满了轻盈与哲思。傅菲的文字则是从自然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文字本身就是自然的肌理,却又不令读者觉得沉重。如傅菲在散文《报秋》中所写:“燕尾与河乌常见,不常见的是池鹭。池鹭是独行客,翅羽如蓑衣,头羽如斗笠,以芒草做掩护,在溪涧觅食鱼虾和蛙类。芒草在簌簌地响动。那是一个清凉的世界。溪涧羸弱,水流似有似无。它常栖之地是池塘。荷叶田田。池鹭隐在荷叶下,等鱼游过来。它是最古老的渔翁。”
傅菲对自然的描写细致而绵密。他刻写自然万物的风情、风度,传递自然、生命以及与生命发生的温暖情感,并以中国式的智慧探寻中国人的自我安慰和超脱,将人在自然中的惬意和自渡精准地呈现出来。这种散文创作风格也是有迹可循的。傅菲曾在《每一个作家都是大自然的布道者》一文中说:“我始终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即,每一个作家都是大自然的布道者。”“山林会在某一个瞬间,被我吸进五脏六腑,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人文和自然的交融使得傅菲生态散文既凡俗又脱俗,诗意盎然,生气弥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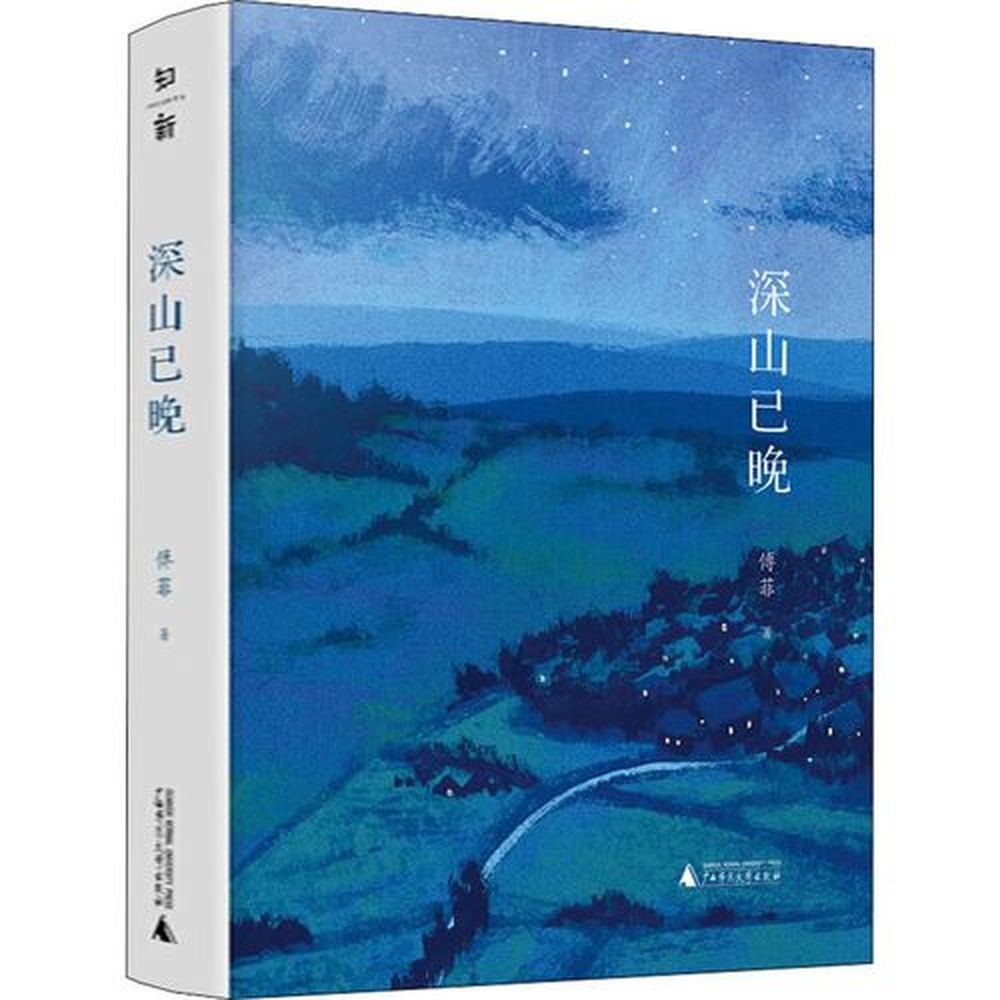
对于自己的身份,傅菲在散文集《深山已晚》的扉页自我介绍:南方乡村研究者,自然伦理探究者。这是作家自我的身份认同。如此,我们读到了傅菲笔下富有人文性的生态散文。
青年作家周华诚的散文也执着于书写自然万物。《把秧安放进大地》一文中写道:“低头和弯腰是与田野进行亲密接触的首要条件。弯腰使得人呈现一种躬耕于南阳的低微之态,低头是把视野变小,把世界观变成脚下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水,看见泥,看见水中天,看见天上有云,看见水中有自己,也看到水中有蝌蚪。”
从周华诚的文字中可见作家对自然万物的浸透与感悟。评论家王兆胜说,这不是简单的回归田园,也不是陶渊明式的与自然融为一体,而是经过现代思想熏陶后的觉醒与超越,是诗意化的现代栖居。
近几年,越来越多作家执着于书写自然中的植物、动物的散文。这些文章像蓬勃的小草一样成长和蔓延,也开出五颜六色花朵,再热烈地拥抱这个世界。
书写“家乡的自然”
多数作家并没有如刘亮程、傅菲这种长期生活在乡村或从事乡野调查的经历,他们书写自然,书写的是家乡的自然。
很多不以写散文著称的作家也有优质的散文创作,他们少年时期多生活在乡土社会,因此散文很大一部分是追忆故乡的自然风物。迟子建在散文集《好时光悄悄溜走》中写道,很幸运自己的童年是在山里度过的,家乡的风雪、草木、山野都给了她极好的生命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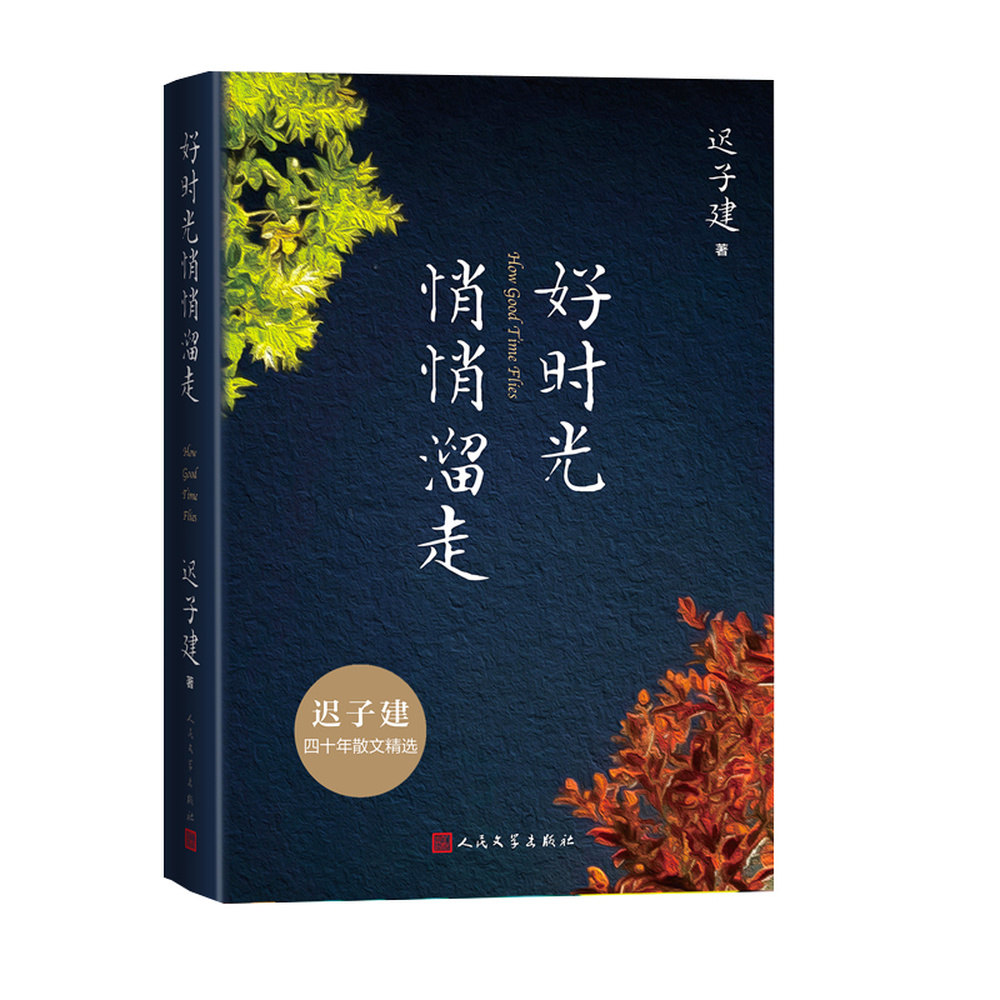
看迟子建在散文中对家乡风物的记忆和书写:“我最喜欢自己拉着爬犁上山拉烧柴。带上一把锯,不用走太远,就可以伐到水冬瓜。青色的水冬瓜很好伐,如果锯齿比较锋利的话,几分钟它就会扑倒在地。水冬瓜的枝条很脆,你不用斧子就可修剪。把锯转个身子,用锯背去砍枝条,唰唰唰地,那些枝条就像被剪掉的头发似的落在雪地上了。”文字之中荡漾着无尽的野趣和活力。
198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是最后一代还与乡野自然有交集的人。出生于皖南乡村的作家沈书枝近些年出版了《拔蒲歌》《月亮出来》等自然散文集。在这些文章中,如今生活在城市的作者用文字重新搭建了童年的乡村世界:儿时山中的野果、父母饭菜的味道、过年过节的风俗与故事、季节变换时的温情细节,曾经村里的养蚕热,童年可以吃到的桑葚,一一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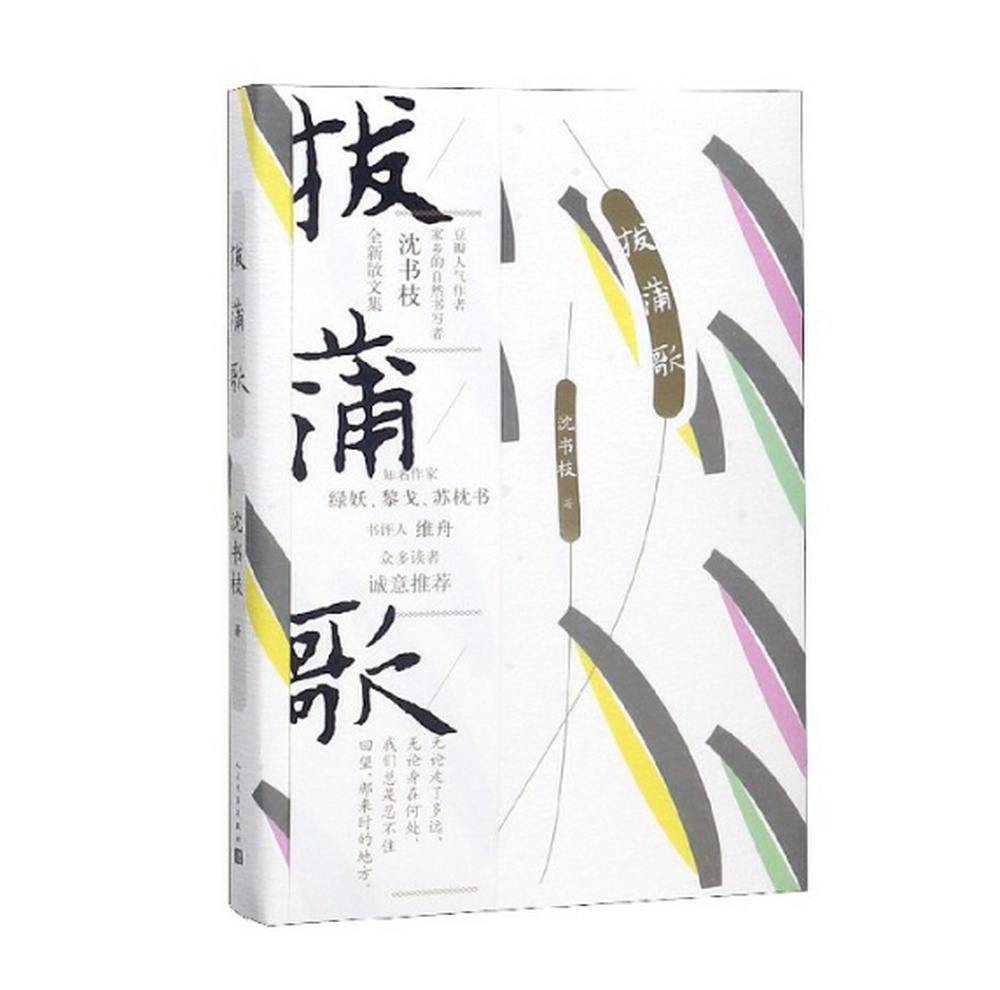
如《蒿饼青团清且嘉》一篇,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回到了在乡间采野菜的童年和春天多雨的皖南地域。“家乡地处皖南,三月春山发绿,雨水渐多,在雨后烟岚笼罩的山里,映山红花开了。这时节倘若坐车从山中经过,每隔一小会儿便可望见一丛或几丛幽丽的映山红花,在新旧参差的绿林中,一闪而过。蕨禾初生低矮,端头蜷曲如小爪,藏在山坡上旧年干枯的茅草丛中,需要低头仔细寻找。”这是属于春天的、浸润着淡淡雨水气息的文字。
当这些较为年轻的作家书写乡野山林时,他们的文字中会有很多乡村生活的细致描摹,而这种描摹与傅菲自然探究的性质还不同,我们从中读到的更多的是——留恋。没错,是对浸润在自然中的童年生活的深深留恋。对农耕文明的回望,对乡土社会人情的赞美,对自然风光的赞美,是当下很多散文作者驻足的地带。某种程度上来说,那已经是藏在时代角落的记忆,沈书枝用文字勾出了那些细腻的画面,让曾经感受过那段生活的读者还会为之心动。
无论是刘亮程的自然哲思散文,傅菲的充满山野调查气息的生态散文,抑或迟子建、沈书枝等作家回望自然的故乡的散文,都让自然散文这座百花园五颜六色、斑斓多姿。阅读这类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是来自大自然的澄澈和活力的阅读感受。
摄影:徐征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