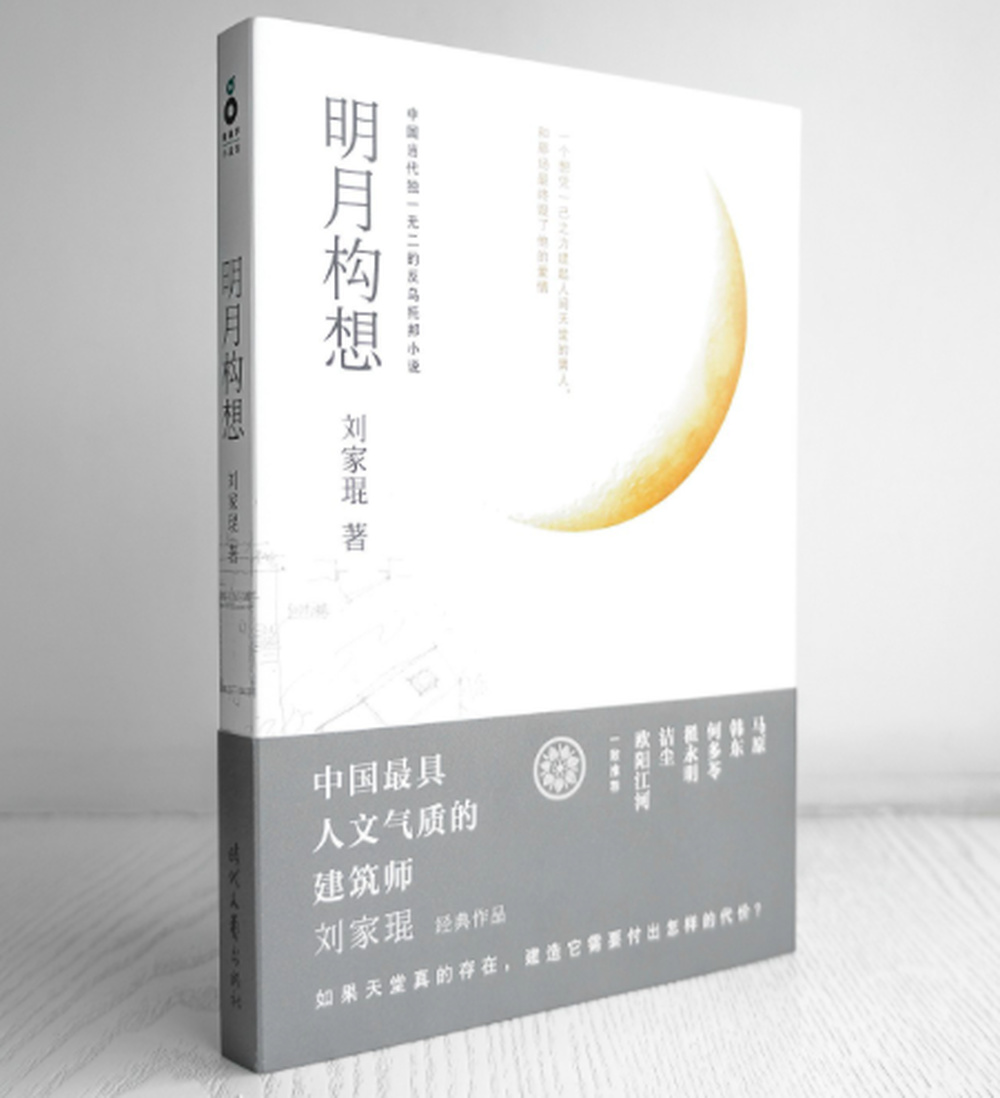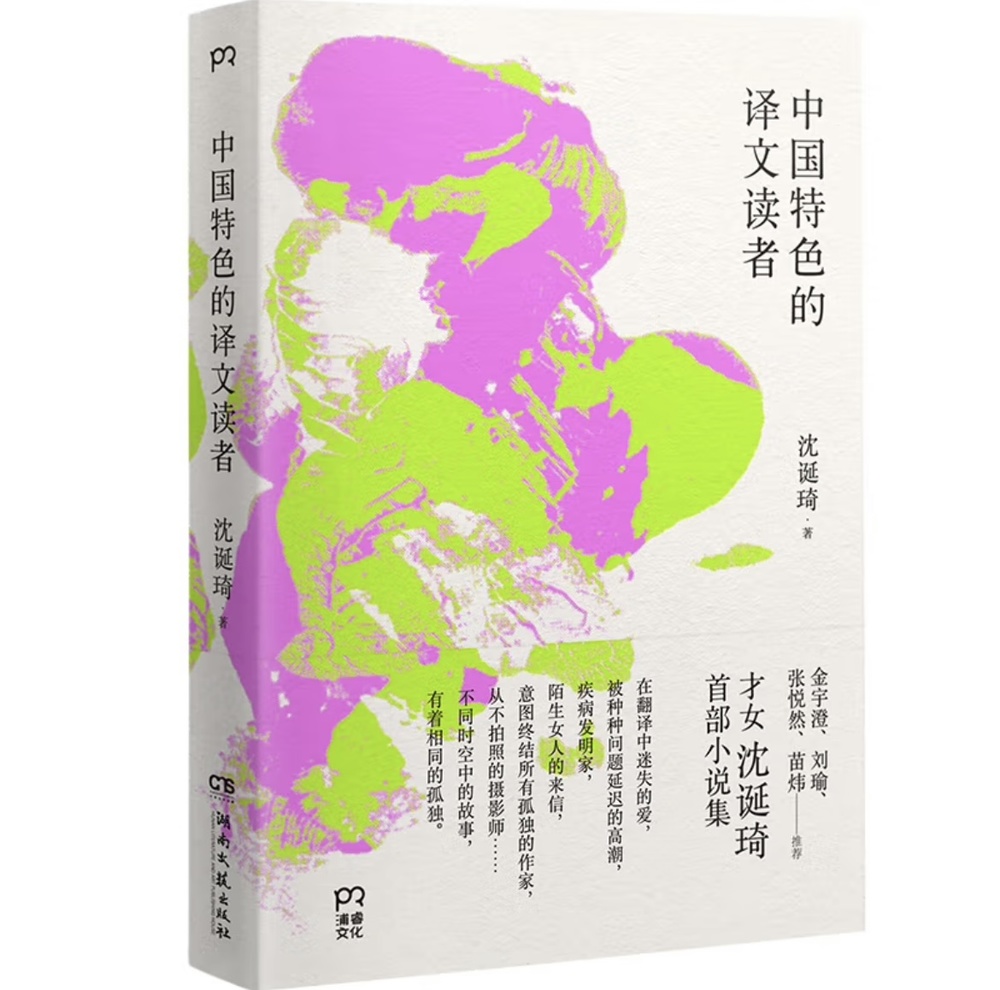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江丹
在网络上搜索“玑衡”。第一页的信息大多指向一种名字为“玑衡”的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两条指向它的延伸意义——衡量事物的标准或准则。如果是前几年,大概率会有一条信息是关于一位写作者的,它是沈诞琦的笔名。
把“玑衡”换作“沈诞琦”,继续搜索。她在这个门户网站上的最新信息停留在2020年,她在为一家媒体写博客专栏,再往前就是2016年,那一年她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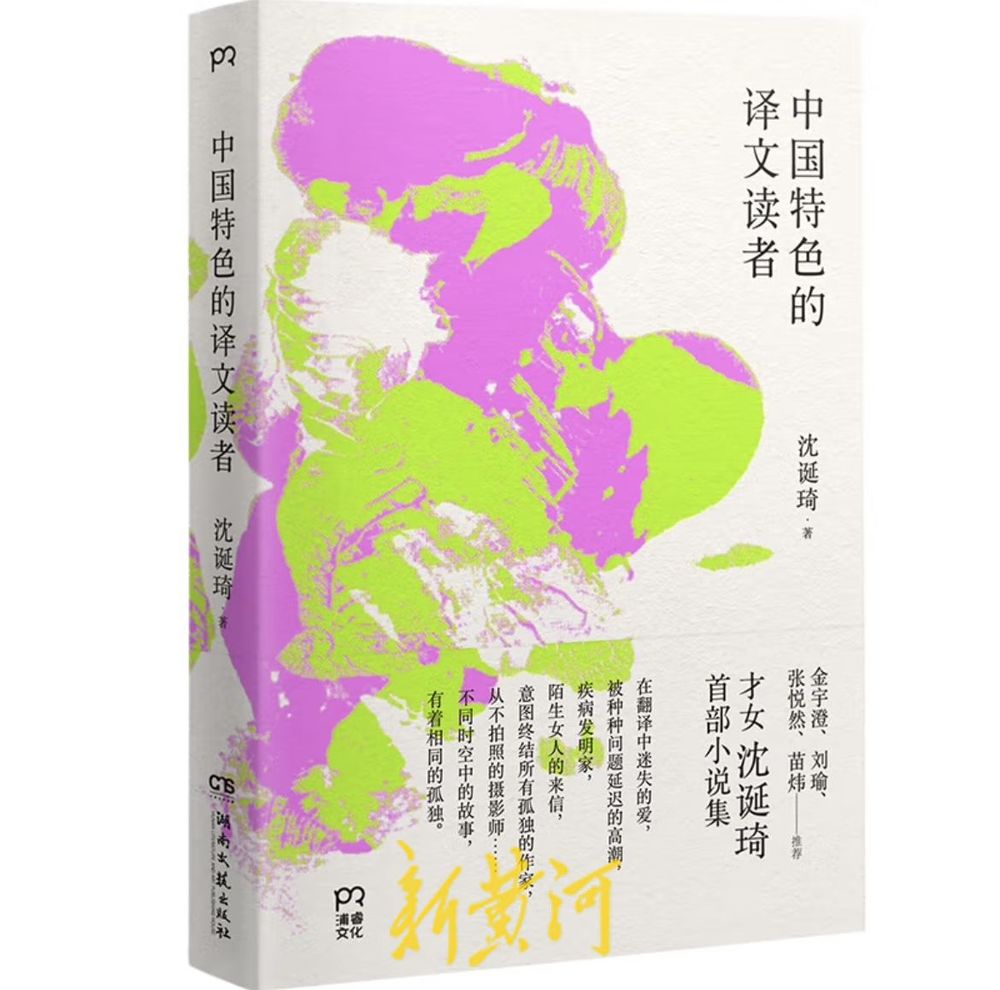
第一次读《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时,是在2016年的一个长假里,每天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可以在台灯下翻翻书。这是一本结构精妙的小说集,沈诞琦在书里讲了很多个故事,但它们实际上又是同一个故事,她平等地对待里面出现的每一个名字,讲述名字背后的人生。
小说集的主题是孤独。语言的壁垒会生出孤独,生活的境遇也会生出孤独,人与人之间也总是隔着千山万水。“他的祖父是个卖唱的戏子,在人前唱尽了动听的曲子,在家里几乎是个哑巴。他的曾祖父,一个养鸭的,天未亮就撑着蒿子把鸭群赶到水中央,鸭子在聒噪,而他默默坐在船里,坐完了一辈子。这么多孤独。也许所有人生细究之下都是孤独的。宋祈轻信了鲁宾的话,以为有一种惊人的孤独可以总结所有的孤独,他梦想亲手揪出这种孤独,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揪出兔子。而孤独逃出了他的手,把他围起来。”
近十年之后再读《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时过境迁。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经历了无数大事小事,唯有孤独不变。只有它,一次次跃过时空,直到成为人生的主题之一。大概没有人会刻意寻找孤独的存在,除了小说家,他们把难以名状的情绪写成一个个故事,制造人生与人生、情绪与情绪之间的互动。
有的孤独是因为失去。《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之后,沈诞琦再没有中文作品出版。许多读者会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位喜欢的作家,也“失去”了曾经与之有所交集的那些部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用“玑衡”这个名字进行写作的沈诞琦向读者展示了一种远方的生活,但突然有一天,一切戛然而止,原来消失很容易,失去亦如是。2016年的读者不会想到,无论是坐在沙龙中间做宣传的作者,还是他们手里的这本书,都会成为被悬置的一个人生片段,所谓的寻常会在后来成为怀念的遗憾。如果继续追溯,博客、论坛这些在互联网初兴时代真正地曾经在人与人世间建立起超越时空链接、帮助很多人打开新世界大门重塑知识维度的网络聚集地,也在人们后来的生活中悄然退场,而新的东西总是来得轰轰烈烈,一次次颠覆人们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说,孤独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节奏的错置吗?我们总是慢一拍或者快一拍,没有与变化同频。特别是在今天,似乎每个人都身处一种剧烈的变化中,我们是该走得快点赶一赶,还是该停下来等一等呢?而我们对这种变化的判断又如何区分正确与错误呢?
在《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这部小说集的同名篇里,主人公何杨的童年和少年只能读质量参差的译本小说。十岁那年,何杨读了一套四册黑封面的《飘》,多年以后,她来到《飘》的故事所发生的美国,生活在小说中郝思嘉所居住的城市,可她再也不会重读那一版的《飘》,“因为她担心自己更加精致的成人的品位将很快看出那个版本的粗糙可笑,然后它就失去那种魔法,那种永恒的安慰的作用,这个快时代留给文学的唯一的作用。”但当她沮丧的时候,她还是会用中文为自己打气:“明天是新的一天。”
我们总是在以为寻常的生活里期许未来,我们总是在以为正确的道路上前行。我们总会在遇到一些时刻、到达一些地点之后意识到,变化才是人生常态,“以为”有可能会是过时的计划,没有什么会直到永远,可是,有些被珍藏的东西会渐渐成为一条人生的底线,一次次提醒你不能越界,一次次帮助你战胜沮丧,教会你坦然面对汹涌而来的孤独。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