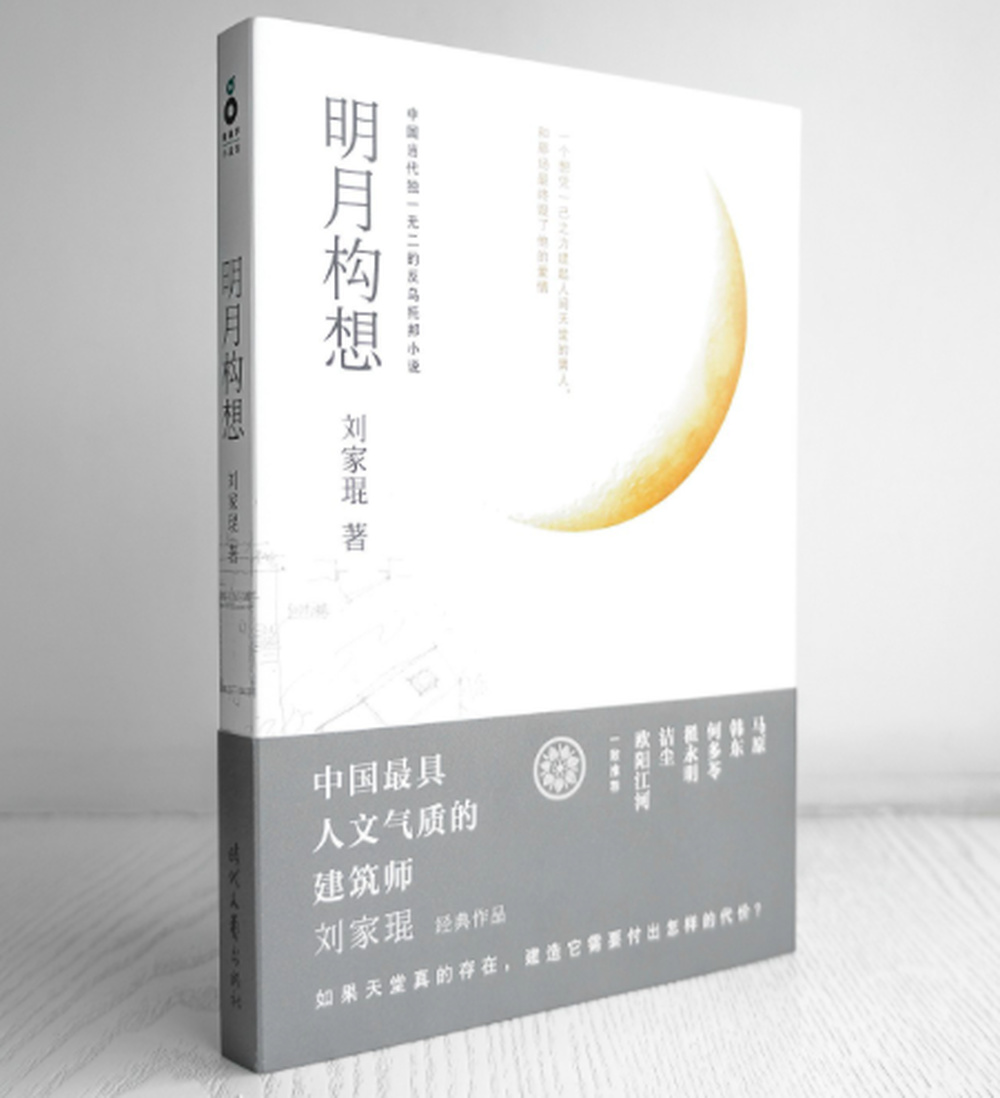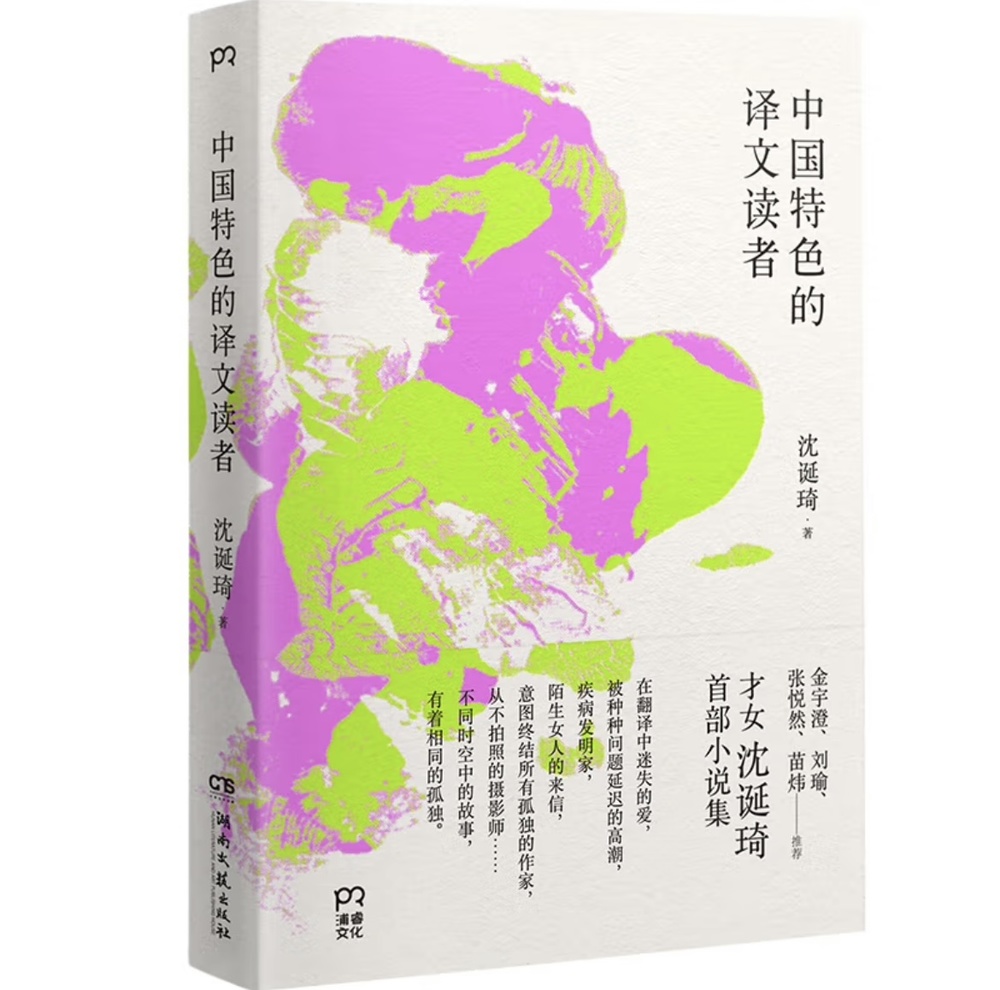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得了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刘家琨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明月构想》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甚至数百元。对常常会随着时间流逝折扣也更低的小说类图书而言,这种“溢价”颇为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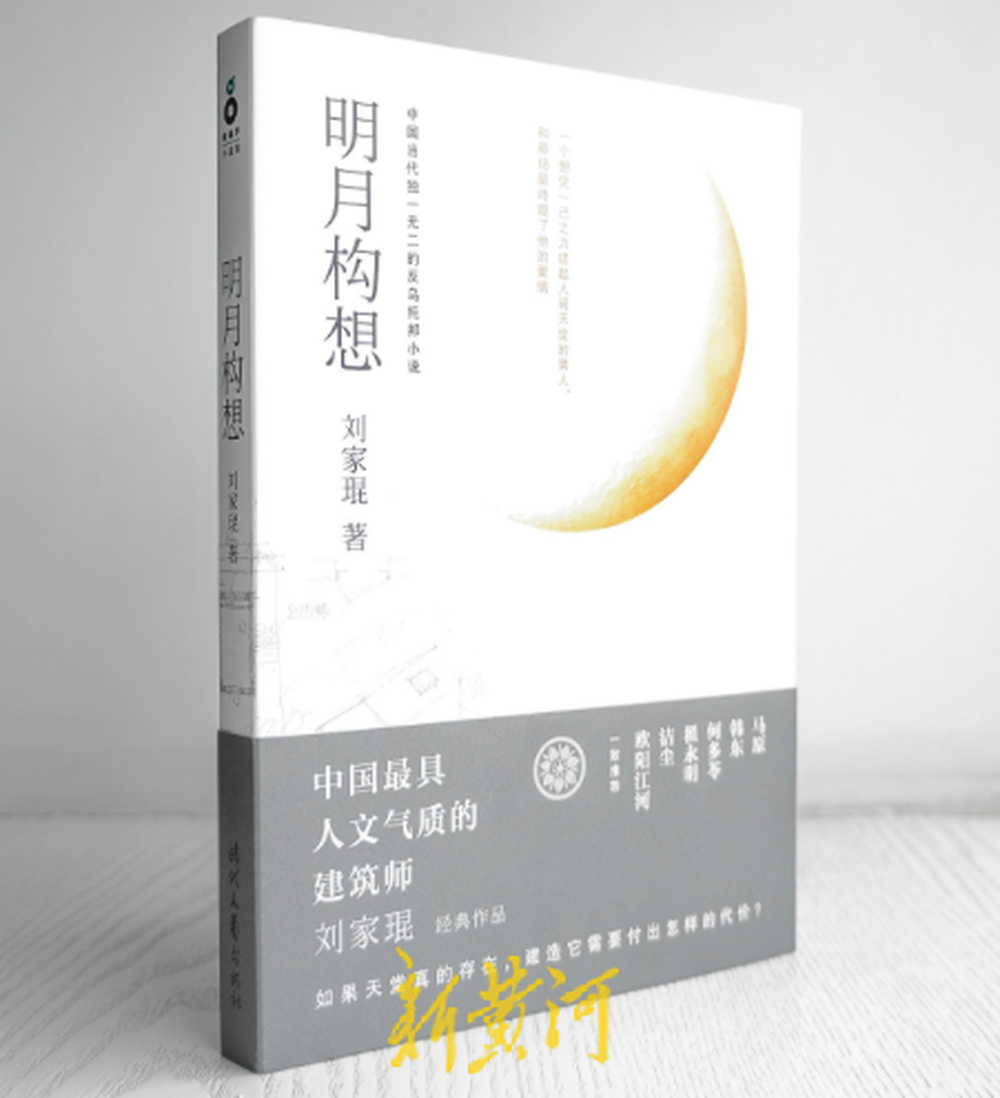
没错,这是一个建筑师写的小说,刘家琨本身就是脚踏建筑和文学“两条船”的传奇人物,在收入《明月构想》一书中的《“我在西部做建筑”吗》一文中,刘家琨对自己的建筑和文学经历有着清晰的叙述和省思。
《明月构想》是一部带有强烈理想主义气质的反乌托邦小说:建筑师欧阳江山要建立一座新城,用建筑重塑人们的灵魂。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被命名为“明月构想”。这位强硬的理想主义者一步步逼近成功,最终却哗然失败。而他的失败,比他的成功更有意义。
印象最深刻的,是小说仿佛一个时代的巨大隐喻。笔触有一种激情燃烧的宏阔气势。仅“明月构想的“徽志”莲花,欧阳江山就有这样的阐释:“这朵从旧世界的污泥中升起的莲花,将体现出新城建设者们对完美无瑕的新生活的追求,体现出信念之虔诚、理想之纯粹,不含杂质。莲花是神话中的宝座,生活在莲花中的人民,将会时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就是宝座的创造者,就是新世界的主人翁。”至于新城的“放射性布局”,更是“宛如钟表”一样精确:“位置随编码的增加而精确,如10923835264,意即十与九大道之间的城区,二环与三环之间的街坊,第八幢三单元五楼二号六口之家中年龄排行第四的那一个人。根据这一原理,还可以细细划分,直至性格和血型。”住在这样的地方,“人们会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看着自己,从而下意识的加强自我监督。”而欧阳江山反复强调的,正是要将明月构想当作一项能改变人性的社会实验,“加速建设明月新城”的同时,是要“突击培养一代新人”。
小说在对明月新城的描绘和项目推进过程的叙述中交织推进,同时交织着对理想的炽热坚持和对隐藏着的荒诞的犀利揭示,并伴随不期而至的幽默。“新战士培育中心”,一顶为群众的夫妻生活专门搭设的帐篷,“脚下是平均主义的薄雪,头上是国际主义的星空“,一对孤男寡女四目相对时的场景,等等,都会“夺目”地刻印在读者的脑海里。
这或许是一本只有建筑师才能写出来的小说,充满了明月新城的迷人细节,这更是一部非有巨大的赤诚之心和犀利的反思能力才能写出来的小说。虽然对围绕明月构想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细节化的描写不够密实,但宏阔巨大的隐喻本身,已足以让小说担得起“中国当代独一无二的反乌托邦小说”的赞誉。
在《“我在西部做建筑”吗》一文末尾,刘家琨这样写道:“建筑设计和写作也许还有更内在的相似:往深处做,关键是找到自己以便放下,做事要发自内心。用废墟材料做‘再生砖’,为普通女孩建纪念馆……都不像以往的设计那样受人委托,搜肠刮肚,而是涌浪一翻就在眼前。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事对社会意义大不大其实都不那么重要,是我自己非做不可。”
如此,则《明月构想》当然也是刘家琨“非写不可”的一部小说,然而不管对作者是否重要,小说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小说引言所写:“结局如此,正如长长的曲折廊道把人们引向一堵光秃的墙,或是拆开层层包装看见一张白纸,这结局把一切奋斗收归为零,令人无言以对。”“明月构想”仿佛已成一代人的“集体隐私”,但建筑师刘家琨用文字让它醒目地耸立在了书页之间。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