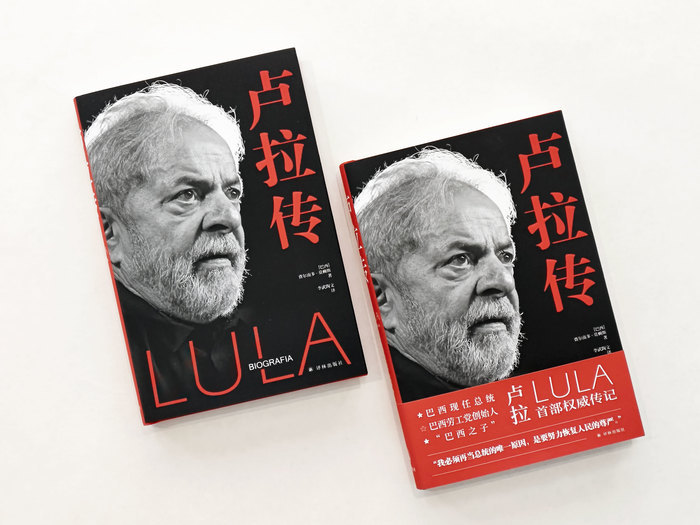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江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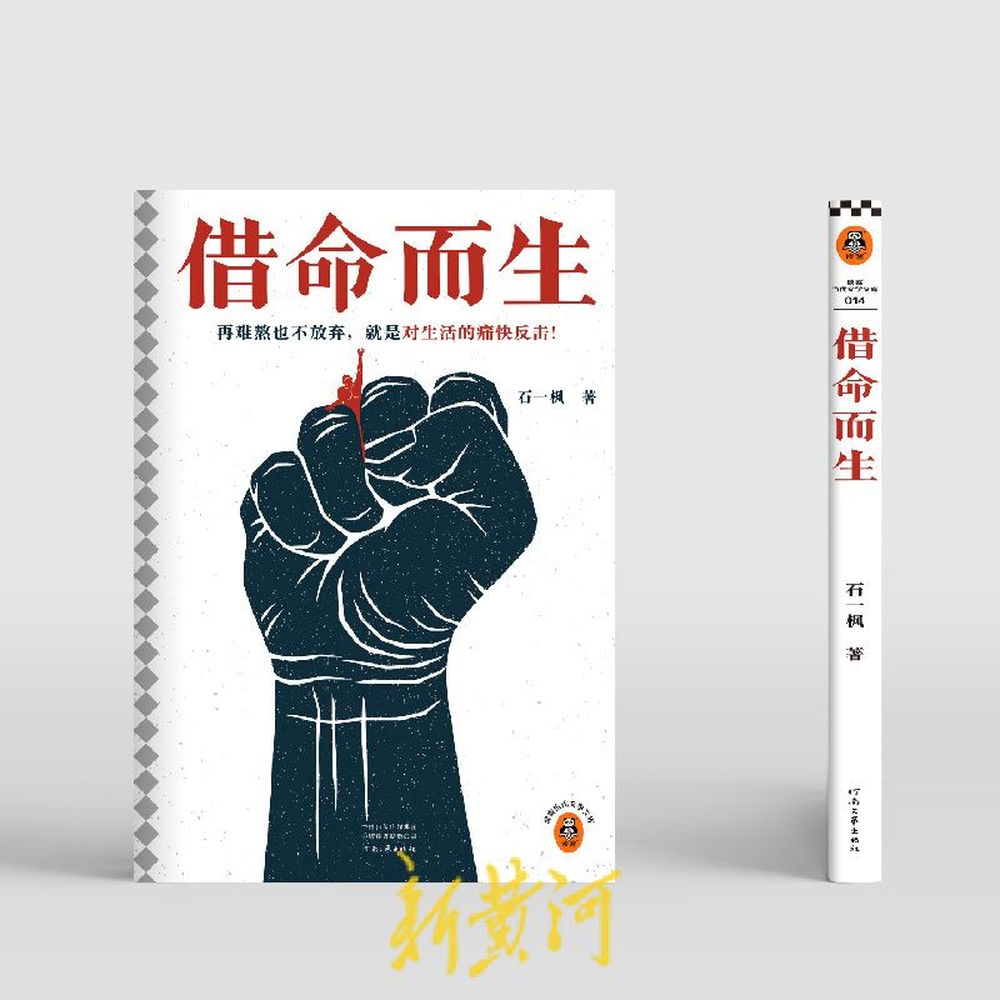
因为影视剧《借命而生》的热播,前几年出版的同名原著小说再次受到关注。
小说《借命而生》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的代表作品,讲述的是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与两名越狱的盗窃案嫌犯姚、许之间的命运纠葛。1985年,杜湘东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看守所成为一名管教,从此距离他的刑警梦越来越远。三年后,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情烦恼时,他遇到了姚和许。不久之后,这两名嫌犯从看守所逃跑,其中抢走管教配枪的姚被第一时间抓了回来,许却不知所踪。从此,杜湘东不再提工作调动的事,也不再把刑警的梦想挂在嘴边,日复一日,他成了看守所里那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中年人,但是当年一起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在杜湘东心里过不去。直到有一天,许出现在看守所。
这不是一部为悬疑而悬疑的小说,可是等到读者来到书的结尾处时会发现,真正的悬疑并不是姚与许所涉的盗窃案,也不是许潜逃多年归案的曲折过程,而支撑杜湘东坚持寻找许的动力也不是对当年失职的愧疚和弥补,而是一个抢枪的细节,也就是说,姚为什么要抢那把枪。只有真正明白了这个问题,才知道杜湘东为什么无法放弃,才知道作为题目“借命而生”四个字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到底是谁在借谁的命,是许在借姚的命吗,在杜湘东的理解里是这样的,可杜湘东这么多年不放弃地寻找许就只是为了告诉他这件事吗,当然不是。
杜湘东这个人物形象,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都可见得,他是失意的、颓废的,但又是倔强的、执拗的,在他的单线程人生思维里,寻找许是唯一的目标。小说里,他的父母没有出现,唯一的家庭关系是妻子刘芬芳,而他之所以有这段婚姻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姚过程中所表现的英雄光环,而光环终究会消失的。实际上,对杜湘东来说,他也是在“借命而生”,他为了一个户口妥协去了看守所,他顺着光环娶了原本要跟他分开的刘芬芳,他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奋起而做过什么,而姚与许身上有他渴望却没有的东西。
这不是一部为悬疑而悬疑的小说,还在于读者可以在小说里听到时代的背景音。无论是直接描写还是间接叙述的,无论是着重提及还是一笔带过的,读者跟着这个故事重回1980年代,再走一遍1900年代,然后跨越世纪。那些社会大事件不曾被遗忘,它是当时的新闻,也是后来的历史,还是人们所经历过的生活。而当它们出现在《借命而生》这部小说里的时候,读者可以看到一位青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它们或许会帮助加固小说的真实感,增强小说的时间厚度,另一方面,它们又提醒读者不要遗忘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更不要遗忘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些时代。
除了这些时代背景音,很多读者应该还会对小说中的那些“配角”念念不忘。比如“逼急了我也跑”的郑三闯,比如酒瓶永不见底的老吴,比如对贿赂这件事耿耿于怀的徐警官,还有杜湘东的刑警同学、脑袋缠了纱布的保卫科副主任等,就连刘芬芳没有正式露面的二姐都让读者印象深刻。他们不是为了小说情节匆匆出现又匆匆离场的单薄工具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具体的事件、鲜明的语言风格,或者性格等特征。人们在谈及演员的表演时喜欢用“信念感”这个词,而对小说所有人物的鲜活刻画正是来自小说家的“信念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相信自己塑造的这些人物确实在那个场景里生活过,而与之相关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因此他们不是只言片语就可以略过的人。
人们喜欢《借命而生》这部小说可以有很多原因,但基础一定是从中得到了共鸣。其中一环套一环的悬疑线索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固然让一路追随的读者感到酣畅淋漓,但是当杜湘东一次次出现在读者的回味中时,他已经被读者视为另一个世界里的“我”。人们或许会忘记悬疑小说结尾处的那种恍然大悟,但是一定会记得杜湘东这个人物角色。对读者来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借命而生”?总要做点什么,总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才能不枉这短暂一生。
编辑:徐征 校对: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