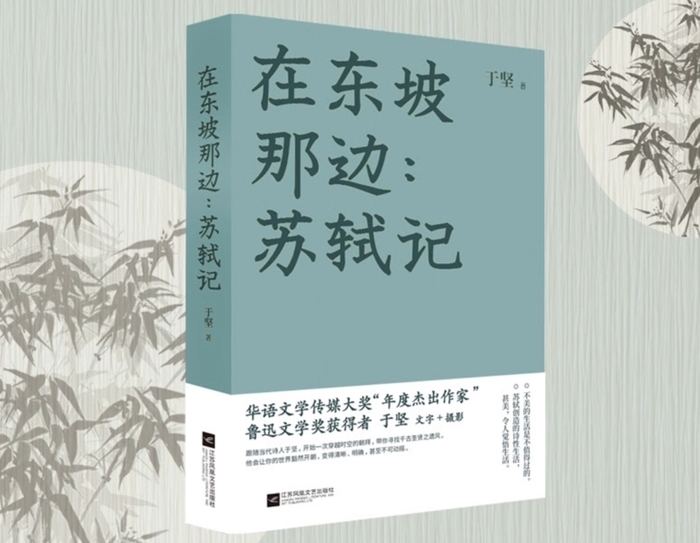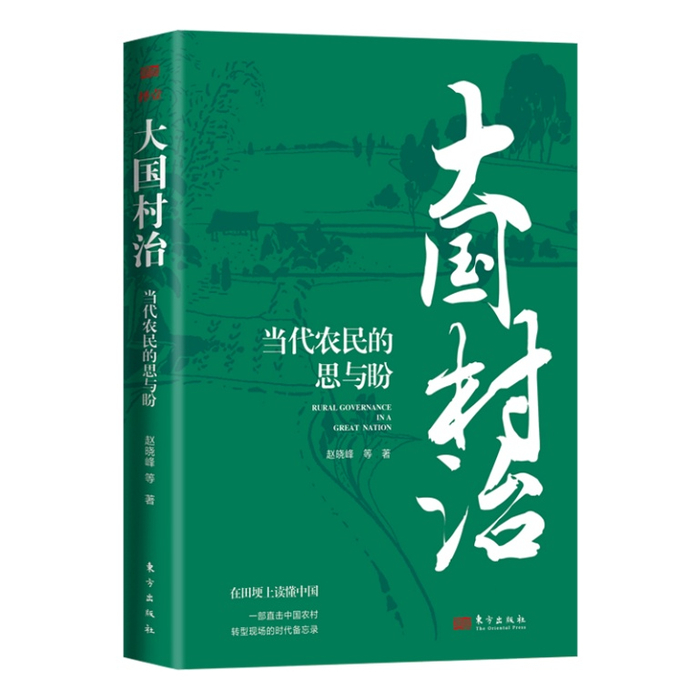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从《建水记》《昆明记》《巴黎记》一路读下来,深以为于坚的行走笔记有一种鲜明的“壮游”气质——在庸常的洪流中,壮阔地行走。换句话说,于坚有一种“处理时代”的能力,有一种呼应那些逝去的伟大心灵的能力,有一种昂首挺立、蓬勃恣肆的气势和风度。
这一本《在东坡那边:苏轼记》也是如此。眉山、开封、杭州、黄州、惠州……一趟追寻苏轼人生踪迹的旅程。当然必须行走在庸常的洪流之中——在开封,“新城整齐划一,切出来的豆腐块似的,以政治商业为中心,宽阔空荡,适合汽车、显要富人,过客、本地居民倒显得只是摆设了。”清明上河园,模仿着《清明上河图》,“也雕梁画栋。只是失去了原图的随意、自然、彬彬有礼,终是过于坚硬、夸张、冷漠、缺乏人气。”但显然,于坚的脚步是要穿越这“夸张”“冷漠”,去老城的某些地段,寻找“残余的昔日生活氛围”,寻找“通过一只只灶秘传下来的无法拆迁的口味”。
穿越“夸张”“冷漠”的方式还有那些大地上残存的遗迹。在眉山,在三苏祠,“虽然历朝历代修复或重建,人们总是依据原样,以同样的土木结构、砖瓦、麻筋,同样的雕梁画栋,各时代或许风格稍有不同,但基本的东西从未改变。”于是,“走进苏祠,瞬间就会感到,此地与外面的水泥建筑群完全不同,世界变了,一种古老的美重新归来。”
更震撼的大地上的伟大残存,来自书中《在巩义访宋陵》一篇,“在黄昏抵达巩义。穿过灰尘滚滚的道路,乡镇企业塞满轮胎的小仓库,激动不安的加油站,野心勃勃、欣欣向荣的小镇,无人问津的农家乐……回到藏在它们后面正在撤退的土地上。……小道上覆盖着干土,淹没了鞋帮。走着走着,忽然间,一块穗子沉郁的地面,一个巨石阵从天而降。灰色的陨石。一群远古的武士、文官、雄狮、大象、马匹、怪兽……或立,或蹲,或踞,排列在大地中央。怀疑停止了,呆住不动,哑掉。圆满、厚重、肥壮、实在、威严、从容、朴素、幽暗、苍凉……怀着信任、职守、自重和暗喜。法度森严。那种气象、质地的出场构成了一种苍老的伟大。……世界意志自黑暗的石头中喷薄而出。”
这样的文字是激动人心的,和众多照片一起,这一场在巩义的寻访是为了捕捉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背景,“自卑的时代看不见宋。如果大地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石头,那么这地面就是值得依靠的”。
和《在巩义访宋陵》一样,《在苏轼故乡眉山所见》也是以照片为主。而书中最主要的《苏轼记》则全为文字,汪洋恣肆。——无论照片还是文字,凝聚的都是作者对精神高度的赤诚追寻。
这种精神追寻的可贵之处,在其来自作者深刻的阅读体验和精神共鸣,“如果人们迷失于自己时代的各种异端邪说的话,那么一旦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就会幡然醒悟。”这篇文章是苏轼的《前赤壁赋》,于坚说,当他读这篇文章时,“年轻时代的理直气壮、目空一切,即刻在这位一千年前的作者的汉语面前轰然倒塌”,“当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我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世界观清晰了,确定了,永远不可动摇了。”
不同时空的精神呼应和共振如此强烈,持续不断涌现在作者对苏轼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寻中。在于坚看来,“生活就是他(苏轼)的文章,文章就是他的生活。他的文章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文章,而是李白说的‘大块假我以文章’,生活就是艺术。”“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样的文章,本就来自阔大、酣畅的内心,来自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生命形态。
是的,经由苏轼,于坚在思考和追寻的,是诗性的生命形态,苏轼认为,只有诗性的文才可以保证生命的“丰美盛大之乐”,恰如荷尔德林的名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于坚认为,这是一种超越单向度的“赤裸生命”“技术生命”“政治生命”的“诗性生命”,“在中国,这种生命形式自庄周就已被深刻地思考,为中国文人所践行”,而苏轼,“是一个伟大的典范”。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功利、喧嚣、拜物教盛行的时代,一个“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不美的进步……人们渴望生活”的时代,人们当然会继续如于坚这般凝视并追寻苏轼这样的诗性生命。
人们当然也能体会苏轼自谓“鏖糟陂里陶靖节”的况味——即便世界如此“鏖糟”,也要让生命走向阔大和诗性。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