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2025年5月,文学新人刘楚昕凭借长篇小说《泥潭》获得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在颁奖典礼上,刘楚昕的发言视频广为传播,“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与此同时,《泥潭》也备受关注,仅预售就达到30万册。
《泥潭》这本书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没落贵族旗人恒丰、社会新力量革命党人关仲卿、旁观者神父马修德等被社会动荡裹挟时的混乱与迷茫。小说吸收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尝试闪回、解离与复调等写作方式展示了人在困境中的复杂和自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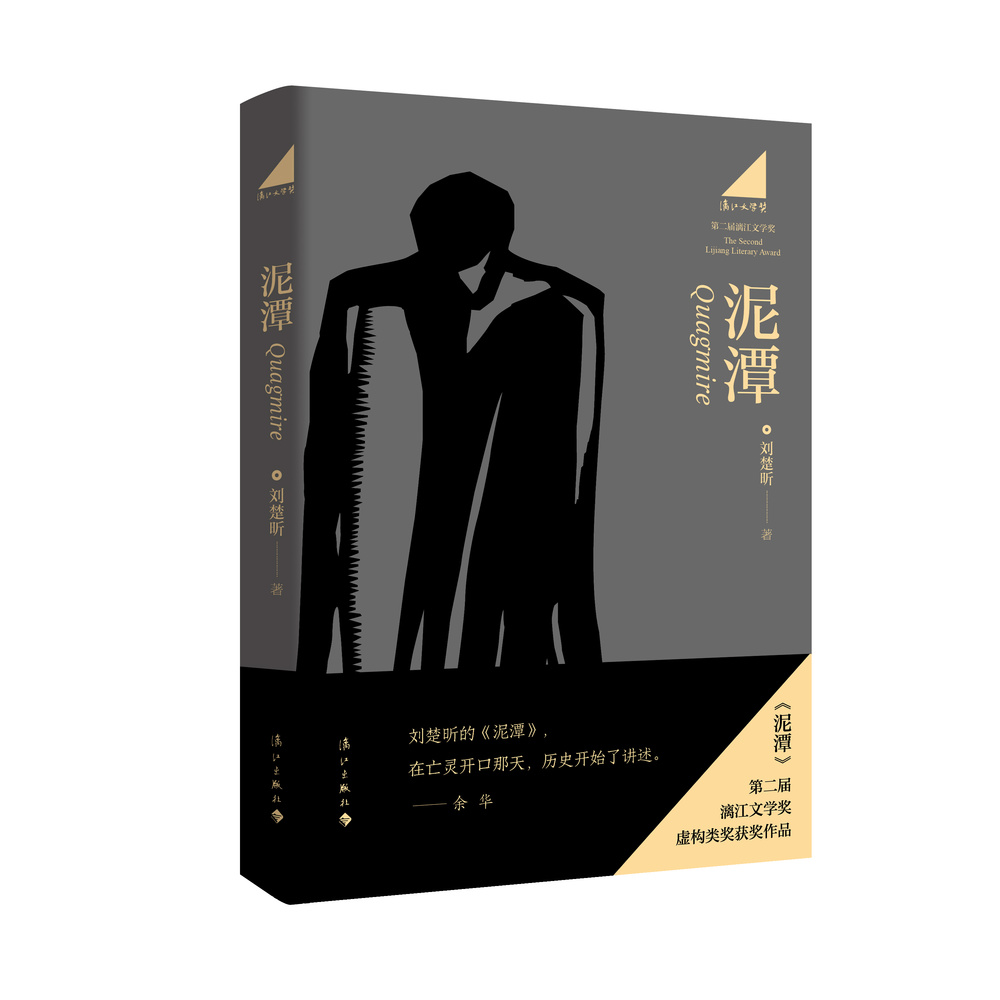
小说三个板块互为映照和交融
据刘楚昕透露,《泥潭》这部小说原有长达50万字的篇幅,经过六年的反复修改,如今呈现出来的是17.4万字。
《泥潭》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间和地点,可以笼统概括为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在武汉的时代碎屑。小说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具体时间坐标是武昌起义前后,叙述视角是落魄的前旗人军官恒丰。这一部分使用了双视角叙述结构,一条是恒丰本人,另一条是恒丰的亡灵视角。两条叙事线索交叉并进,会带给读者“闪回”的阅读体验。整体看来,这一部分主要呈现了当时武汉的政治环境,革命洪流之下普通人随波逐流的命运,以及如草芥的生命。
第二部分的时间线索较长一些的,大致从清末留日时期到武昌起义之后。这一部分的叙述视角是革命党人关仲卿,讲述了关仲卿日本留学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因为思想差异与友人乌端的绝交。起初他也将革命视为拯救个人与社会的唯一出路,不过随着革命的进展,关仲卿也开始变得踌躇起来。渐渐地,革命对他而言,从“救赎之路”逐渐变为另一个无法挣脱的泥潭。
第三部分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时间是1935年,叙述视角是神父马修德。这一部分中,马修德以日记的形式回忆了自己漂洋过海来中国的经历,讲述了恒丰对马修德的一些人生忏悔,以及恒丰妹妹的一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惨痛经历。同时,这一部分对前两部分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收束,某种程度上让这三部分从结构、内容上互为映照,浑融一体。
小说整体上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展现了普通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困境。虽然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叙述主体,不过这个主体也并非绝对的小说主角。小说以群像式手法叙事,人物看似独立却又存在千丝万缕联系。作为读者,如果对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前后的武汉状况有所了解的话,阅读起来才会比较顺畅。就整部小说而言,读者也必须在整本书阅读完毕之后,才能串联起几个重要人物的生命经历,以及几个板块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从而领悟到作家对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的用意。
复调的叙事和实验性的语言
《泥潭》的腰封上印着著名作家余华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刘楚昕的《泥潭》,在亡灵开口那天,历史开始了讲述。
如余华所言,小说的第一句话,或者说第一篇章的内容,均是亡灵视角:“如您所见,我死了。一九一二年五月,八号还是九号,不知道。傍晚,我被两队巡警逼到公安门西侧城墙脚下。我颤抖的怒吼刚沉寂没多久,五个巡警抬枪朝我一轮齐射,接着拉动枪栓,又是一轮。枪声停了,呼喊与脚步声乱哄哄持续着。”
这部小说,或者说重点是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尝试了多种叙事手法——闪回、解离与复调,将文本置于浓厚的探索氛围之中。在不同的板块中,作者间杂着呈现几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又可以与其他版块的书写连缀起来,拼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以及如复杂慌乱的社会图景。
第一部分的亡灵视角与回忆中的恒丰视角交错并行的结构最为典型。这种写法让读者在两种不同的文字氛围中进行切换,增加了文本的纵深感,客观上也提高了阅读门槛。此外,小说中还夹杂了不少亡灵视角中的意识流的写法,即一段话没有标题符号的写法,如:“对北方的怀念只持续了一代后来的子孙很快习惯了南方的气候之后又过了两代人据京城外放到此做官的旗人评价我们的口音已经受到南方话的影响略微改变了又过了一代人后代的某一支取了恒作为汉姓以与其他宗族区别。”这种写法很明显借鉴了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意识流的文本写作方式。
对于不少读者讨论的亡灵视角的叙述,刘楚昕也在漓江出版社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做出了解释。他说,亡灵在任何时间空间都可以出现,回忆中的“我”才是第一视角,相当于从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同时来写这个故事。“亡灵还代表了一种病症,表示一个人处在精神分裂之中。亡灵还代表了一种反思。亡灵其实就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自己在审视自己,代表了反思和道德审判的意味。”
刘楚昕同时也谈到,写作必须吸收现代派的写法。“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如此,我们才在《泥潭》中读到了大量复调的写作手法以及颇具实验性的语言形式。可以想象,作为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作家一定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构思与打磨。尽管这些写法在文学上并不算创新,作家对这些的驾驭也并不是那么娴熟自如,这依然是当下历史小说书写的较为少见的创新方式。
小说想唤醒人们直面生活
如果说写作手法和语言上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实验属性,带给读者些微陌生和具有障碍的阅读体验;那么从内容上来说,《泥潭》无疑是让人感受到窒息和沉重。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无论是革命党、旗人、车夫、掘墓人还是妇女,都深陷的时代的泥潭之中苦苦挣扎。这种挣扎不仅是物质和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时代的洪流下普通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小说也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说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
小说怎么写固然很重要,想表达什么也非常重要。作者刘楚昕是一名哲学博士,从其作品中以及相关言谈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哲学的痕迹。如刘楚昕所言,《泥潭》是在深刻追问存在的意义:人总是被突然抛掷到某个境遇,必须做出某种选择和承诺,并为此承担后果。正是在这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中,生命的意义与自我拯救得以显现。
如果笼统地总结《泥潭》的内容,那小说就是写了三个人的死,一个是旗人,一个是革命党,一个神父。三个小人物的死反映整个时代的变化。“死亡给了我们重新看待生活的一次机会。”刘楚昕说,人生漫长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死亡可能会在任何时间悄然到来。小说和他的理念都是要唤醒大家,从这个幻梦中醒来,直面生活,并且重新反思和珍惜现在的生活。而如康德所说,我们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泥潭》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生活就像在沙子里面找金子一样,正是那些高贵的品质,哪怕是一闪而过的,人类所展现出来的高贵的品质,支撑着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小说也是传达这样一个信念。
虽然刘楚昕还算是一名文学新人,但是他的写作时间其实已经持续了十余年。可以感受到,刘楚昕的文学创作不是喷薄而出的类型,而是纳入很多关于历史、社会的思考,以及文本创新的尝试,这也导致一部小说最终成稿之前会经历“漫长的拉扯”。对于一名年轻作家而言,这些是真诚而可贵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写作淬炼,刘楚昕未来可期。
编辑:任晓斐 校对:汤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