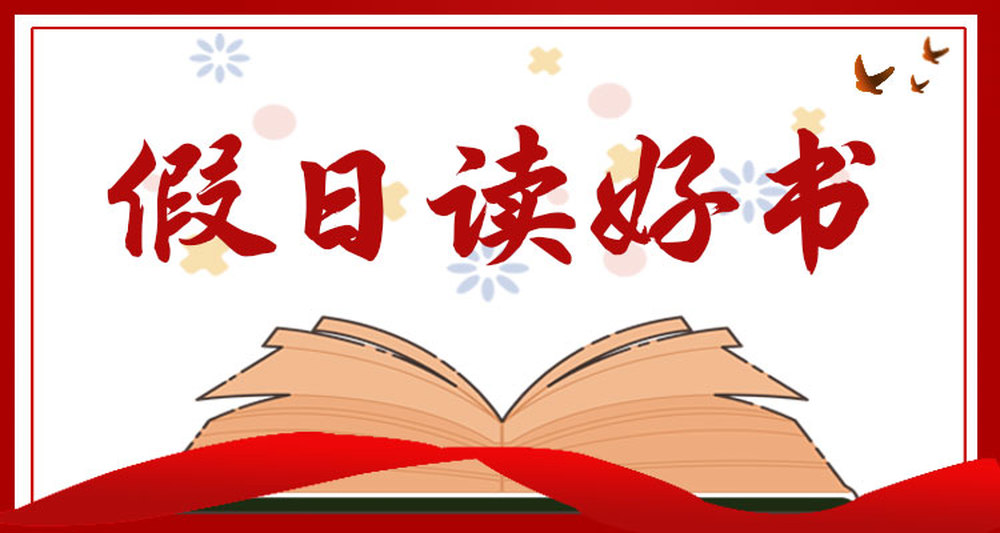作者:姜志强
王方晨《快雪时晴》是一篇能让你掩卷长思,余味如陈年老酒在心头百转千回的文字。妙处不在情节之繁,而在意蕴之深;不在言语之巧,而在风骨之正。此文之魂,窃以为可从“舍”“得”二字勘破。
通篇读罢,不禁长叹。这哪里是在写一个叫“老竹”的民间书法家,分明是在写一种久违的中国文人精神的现代回响。他是作家在现代都市的喧嚣背景下精心塑造的一个趋近于“真人”的形象。他的一生就是一场不断“舍弃”的修行。
其一,舍功名利禄。年轻时的老竹,厂长器重,文化馆欲调,可谓是前程似锦。时代巨变,女工抛弃,让他“舍”去了这一切。这是被动的“舍”,是命运的无情剥夺,逼他回到内心,回到那一方只属于他的书桌,“因祸得福”,得的是艺术上的专注。
其二,舍爱恨情仇。小说写了老竹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层次分明。第一个女工是镜花水月,她的离去是他“求不得”的痛苦。第二个女人小梅给了他短暂的婚姻,也在他的心上又添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疤。面对这两次情感的重创,老竹没有沉沦于怨恨。他只是默默地在雪地上写下“小梅”二字。这“舍”,是舍掉了怨念。不怨,方能自救。
第三个女人菊,是老竹生命里的“时晴”。“你写你的字”,尘世间最温暖的懂得。然而命运再次“快雪”,菊的离世是老竹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击。这次他选择了一种最决绝的“舍”——他烧掉了满屋子的字,撅折了毛笔,倒尽了剩墨。
这一把火烧得好,烧掉了过去的名声,半生心血,更烧掉了心中对笔墨纸砚的“执念”。
“舍”到了极致,便是“得”的开始。屋子空了,心也空了,再无挂碍。他开始在空中比划,这便是“空书”的由来。他从一个在纸上追求技巧的书法家升华成了一个以天地为纸、以心意为笔的“真人”。舍弃了“形”,却得到了“神”;舍弃了“术”,却得到了“道”。他的人生,终于“快雪时晴”,一片澄明。
这篇小说最奇崛、最精妙的意象,作者的神来之笔,就是老竹的“空书”,直接将小说境界提升了一个层次,虚实相生,营造了文学的奇境。
“空书”是虚的,真正的艺术到最后或许根本不需要物质载体。它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与宇宙的对话。
“空书”又是实的。它虽无形,却有神。当他在空中写下巍峨如山的“小梅”二字时,那份积压了几十年的宽恕与深情,其力量足以惊天动地。
“空书”的妙处在于它完美诠释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虚实相生”。空无一物的空气因他的书写而充盈着万千气象;无声无息的动作因他的心意而回荡着雷霆之音。
《快雪时晴》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写了当代美好的“知音”关系,阐释了人生的“渡”与“归”。知音是这篇小说中另一束温暖的光。
阮阿庆将老竹从个人的悲苦中“渡”了出来,让他知道,在这世上他不是孤身一人。当阮阿庆的胡琴被撅折,他也从“有”入“无”,开始在空中“无声拉弦”。妙哉!这二人最终在精神的最高处殊途同归。他们证明了,只要“一颗心”还在,弦就在,笔也在。
而小梅的“归”,则是对老竹人生的圆满。如果说阮阿庆是精神上的知己,那小梅的回归则是尘世间的慰藉。她对老竹说,“我来看看字。”这句话意味无穷。她看的不仅是墙上的字,更是写字的人,是这个人背后的岁月。
老竹最终的原谅是他“舍”的最高境界——舍掉计较,完成了对人性的终极宽容。这“归”,让老竹的“真人”形象彻底落到了实处,有了人间的温度。
《快雪时晴》全篇弥漫着一股清气,传达了当代道心,那就是传统文人风骨的现代回响。小说通过老竹这个人物,深刻地探讨了在高度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里,一个有风骨的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
其一,对抗“唯利是图”。老竹唯一的坚持就是写字,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正是对功利主义最有力的反抗。
其二,对“情义”的坚守。老竹对菊的承诺,对阮阿庆的知音之情,对小梅的最终宽恕,都体现了“情”与“义”。他烧掉那幅价值不菲的字帖时,分明是在进行一场自我灵魂的洗礼,精神的祭奠。这一“化”是全篇的点睛之笔,是人格的升华,其光芒足以烛照人心。
《快雪时晴》是一篇以小切口写大格局,以“真情感”承载“深哲理”的佳作。它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对艺术的虔诚,对知音的珍视,对爱与宽恕的坚守,以及那份在历经风雪后安顿身心的澄明与坦然。
编辑:钱欢青 校对: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