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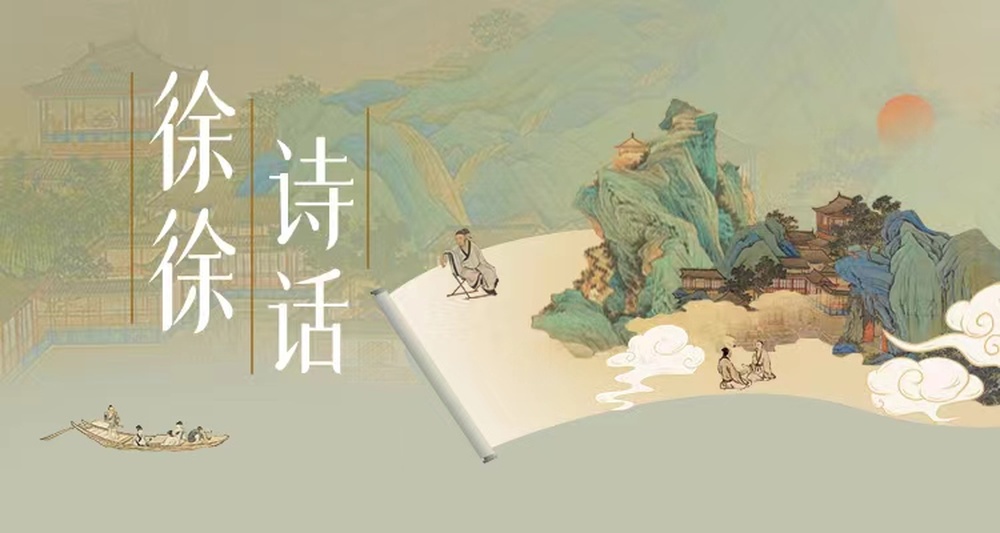
2004年,我第一次在武汉见到长江。看着滔滔江水日夜不息地奔流,壮阔而又深沉,令我生出时间与江水同样浩渺,“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的慨叹。后来看地图获知,长江流经武汉时有一段是往北流,且城市和跨江大桥均是建设在江水比较狭窄的地方。即便如此,第一次面临长江的感觉依然盛大而浩荡。
2024年,我在襄阳见到了汉江,这条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支流。具体地点是孟浩然写下“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的鱼梁州。汉江到了下游水流丰沛,渊深而水阔,江水缓慢而平静地流过鱼梁州,流向长江。望向远处,目之所及江水与天际相连,令人只觉生而有涯,而江水浩渺千载。当年,孟浩然与友人登上砚山看到的大抵也是这番景致。
2025年夏天,在大连飞往济南的飞机上,飞抵济南之前我清晰地看到了黄河入海口。俯视地面,只见一条黄浊的河流往偏东北方向流去,直到水流冲进深蓝色的大海。黄河与大海交汇之处,黄色的河水与海水相遇后迎面回旋,冲击出的轮廓宛如一棵棵黄色的树木版画。果然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化出这般瑰丽的画卷,河流与海洋的高歌不停不息,人类才是匆匆过客。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临水抒情的传统。流动不息的江水特别容易激起诗人们的遐想和感慨,江水从时间深处奔流而来,又向着未知的未来奔腾而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哲思的命题。而无论人世间经历什么样的物换星移,更遑论个人的悲欢离合,江水依然是原来的模样。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在行旅中经过江畔,很容易发出或是失意、或是抒发抱负的诗句。
后世很难超越的一句临水抒情的诗句是南北朝文学家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这句诗出自谢朓诗作《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
风烟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谢朓虽出身于世家大族,不过早早卷入政治斗争,深知其中险恶。当时,谢朓深受随王萧子隆的赏识,在荆州任随王府文学(官职名称),但因遭到谗言而被召回京都(今江苏南京)。永明十一年(493)秋,三十岁的谢朓从荆州返回京都,在这段行程的最后一段,行至临近京都时,谢朓面对浩浩江水发出感慨,写下这首诗。
这首诗起句雄浑浩大,气势磅礴,堪称一句具有经典气象的诗句。“大江流日夜”是写眼前之景,“客心悲未央”则是写诗人的心境。“大江”是自然界中的辽阔场景,“日夜”则是时间脉络中的意象,如果按照正常语序,应该是“大江日夜流”,这本是虽然意象宏大却平平的一句诗,却因为语序调整而点石成金。诗人把“流”这个动词前置到“大江”之后,动词前置一下让整个诗句的诗意流动澎湃起来,江水奔流的画面如在目前。“客心悲未央”一句也是如此,“未央”本就是无尽之意,且发音清亮悠长,二字的形态也非常漂亮,用在句尾别有苍然浩渺之意。这一句诗中,从辽阔的江水到站在江边的诗人,苍茫的空间和时间感扑面而来,格调极高。难怪明代文学理论家陆时雍评价这首诗说:“起四语属高调,然一唱气尽,下无余音。”
说“一唱气尽”未免有些苛刻了,毕竟诗歌需要起承转合和情绪起伏,没有一首诗可以做到每一句都在情绪高点。紧接着第二句的气势就弱了下来,诗人交代了当下的处境,已经离京都越来越近,想要返回荆州已经不太可能。从这两句的口气来看,年仅三十岁的诗人发出的感慨老气横秋——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世事浮沉。实际上,这一年已经算是谢朓人生的后半程了,三十六岁那年他便因遭到构陷而死在狱中。
“秋河曙耿耿”至“玉绳低建章”,这三句写的是即将抵达京都的所见所想,在诗词中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描述。秋夜,曙色微露,水边寒渚夜色苍茫。远远望去,京都的宫墙已经遥遥相望,月光轻柔地照射在宫殿上,星辰则垂挂在宫殿一侧。
“驱车鼎门外”至“江汉限无梁”三句写的是诗人回望荆州,想要回去的话真是长路漫漫。飞驰的日光尚且难以挽留,何况与荆州的同僚还分隔两地。鸟儿可以在风云之间扇动翅膀,大江上却没有桥梁可以通行。总之,诗人想要回到荆州,不过已经隔着千山万水。
起句的盛大更加映衬出后面诗句的普通,不过,最后一句稍微拯救了这些平庸的句子,并且照应了起句。末尾两句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写出了忧惧愤慨的情绪,他把谗邪之徒比作老鹰和秋霜。“寥廓已高翔”写出了诗人性格中的倔强和不屈,虽然也是一句意境宏大的诗句,不过与起句相比,气势还是弱了不少。
编辑:徐征 摄影:王汗冰 校对:李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