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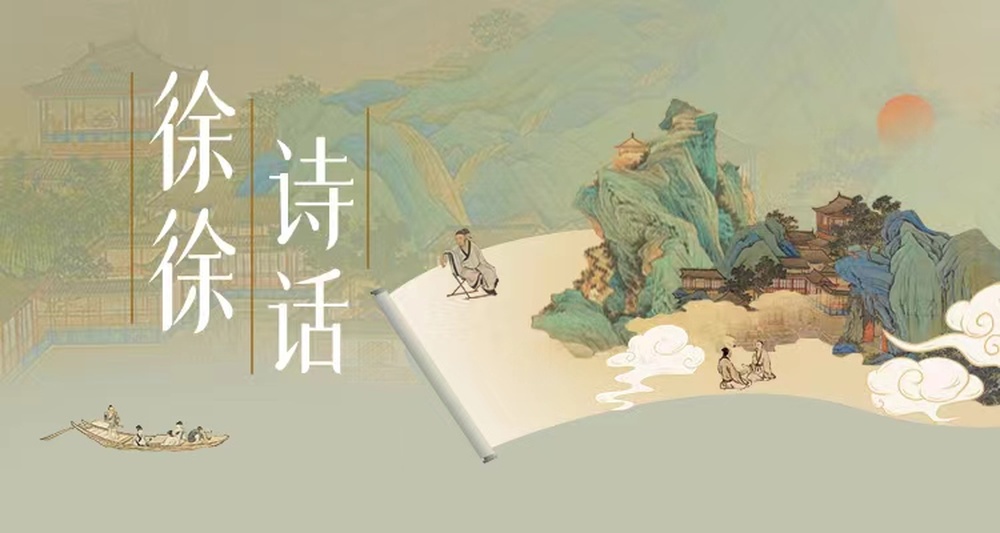
人世间,最美好的季节是春天,最绚烂的植物是花草,最富有诗意的情境是月夜,而最能让诗人内心涌起无限哲思和感慨的,是大江大河。把这些意象串起来,就是“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旧题,原属于“清商辞曲”之“吴声歌曲”。最早以此为诗名作诗的是陈后主,风格与《玉树后庭花》相似,属于宫廷艳曲。后来还有隋炀帝、诸葛颖以及初唐的张子容有作品存留,风格很大程度上洗去了南朝宫体诗的糜艳。陈后主作品已经佚失,另外几名诗人所存作品共五首,皆为五言诗歌,其中最出色的一首是隋炀帝所写: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简短的五言诗中,夜、江、春、花、月依次登场,场景静谧唯美。虽然还有一些南朝乐府民歌的倾向,不过整体上清丽婉转,明净轻快,勾勒出一幅优美的春江月色图。诗人的心情也是轻盈而积极的,整首诗颇有艺术价值。就这类风格的诗作而言,古典诗词专家程千帆称隋炀帝是“宫体诗的继承者,又是其改造者”。不过,隋炀帝以及隋朝多数诗歌仍然是辞藻华丽而毫无筋骨的咏物、咏宫廷琐事的宫体诗,属于文学的末路。
不妨顺着隋朝文学这一切面理顺一下前后一百五十余年间的文学低迷时期。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说,“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制造了这样的宫体诗。”
在这一百多年间,只有北上的庾信写过《乌夜啼》《春别诗》等少量较有气色的作品,然后就是上文中提及的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不过均未能抵抗宫体诗的靡靡之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初,直到初唐四杰横空出世,刘希夷接替,然后最终出现了“绝顶”(闻一多语)的诗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至此,“这首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如此,顺着文学史的脉络,我们可以理解这首《春江花月夜》出现的意义。文学的发展有高峰也有低谷,后人皆是从前代文学中汲取营养,然后改造创新并推向高潮。当面对不可逾越的高峰时,诗人们会拓展其他的路径,开拓出新的诗风。当然,即便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改革创新也是十分不容易的,需要诗人审视当时的文学环境并进行反思,敏捷而超群的才思以及锐意创新的勇气。如此,当一名诗人站在特定的环境中,比如张若虚在一个春夜站在潮水初涨的江边,这一切令他产生了绵渺深邃的宇宙意识以及哀而不伤的情愫,终于诞生了《春江花月夜》。之于文学史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
可以说,《春江花月夜》的出现,犹如在经历了漫长崎岖又枯败干涸的山路之后,倏然看到了一片芳草缤纷的桃花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如今我们都认可这首诗是唐诗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实际上,这首诗的接受史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从诞生之后到元朝的几百年间都是被冷落的。直到清代王闿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中首次提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观点,闻一多称其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的接受与批评才真正迎来繁盛的时代。
从语言、情境来看,这是一首非常好读的诗歌。诗歌前八句写江畔之景,江水、明月、花林、汀沙,充满层次感。接下来八句,从“江天一色无纤尘”至“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面对江天一色,对无穷的宇宙和无尽的时间产生了深远的遐想,这种遐想富有宇宙意识和哲思憬悟,而这一切又没有盖过最重要的诗趣。
从“白云一片去悠悠”开始,诗人重点从景致描写转而书写思妇,写了想象中在明月之下徘徊的女子对离人的思念。“昨夜闲潭梦落花”四句写了思妇现实中的孤寂处境,不过这份孤独仍然是唯美的,而不是悲伤的。最后四句,仍然不知道离人何时回来,思妇的情愫袅袅不尽。“落月摇情满江树”收尾,也令读者感受到诗意仍在那个花月夜萦绕,久久不散。
张若虚用七言歌行体来写乐府旧题,本身就是很大的创新。一首比较长的七言歌行又给了诗人很大的施展空间,诗人面对着江水,尽情地展开了对春、花、夜、月的铺陈和联想。并且,即便是有限的人生面对无尽的时间,诗人的情愫也是昂扬的。比起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显然是一种更积极和旷达的态度。这是属于一个快要触摸到盛唐的时代的声音。
另外,诗歌的后半部分书写思妇,这份愁绪也是轻盈而美好的,而不是沉重且无解的。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盛唐之音”的章节中评价这首诗,“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诗人触及了乐府诗中常见的离人之思,而这份思念在诗意的点染之下,带给读者的是生活中恰到好处的一点怅惘,平和宁静又充满希望的怅惘。
说到底,这首诗今天让我们如此挚爱,因为它营造了浑融、完美的诗歌意境。从这首《春江花月夜》中,我们看到了诗歌的一切可能。诗中有真实地映照着明月的潮水,沐浴着月光的花林,诗人从眼前的实景发散而去,又看到了时光洪流中的大江大河以及天地众生。诗歌中的离情,则是让我们这些读者的情感有了与诗情的接轨之处。那似水的柔情以及朦胧的相思是这么深邃隽永,令读者对唯美的情感和诗意一样欲罢不能,回味无尽。诗人在比较长的篇幅中反复铺陈,制造出了这个成熟而完美的意境。《春江花月夜》在文学经历了长期低迷后浮出人间,昭示着花团锦簇的诗歌的盛唐即将扑面而来。

因为《春江花月夜》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这也导致我们对张若虚其人具体生平经历也知之甚少。后来随着这首诗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界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有学者将这首《春江花月夜》与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相比较,认为《春江花月夜》整首诗的意境,均被张九龄用四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言尽。我们不清楚这两首诗哪首在前,不过这一说法似乎也有合理之处。或者说,一些伟大的诗歌所塑造的意境或者审美境界本身就有相似之处。
“凝练”是诗歌的特质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优势。我们必须承认,在《春江花月夜》反复铺陈勾连而营造出的诗意中,我们感受到的艺术审美也在层层渲染,层层递进。张九龄用四句诗营造了宏大而又绵渺的诗意,这是他的伟大之处。而张若虚的长诗《春江花月夜》亦没有一个废字,它营造了一个个更细腻更绵长的场景,每一个字、每一句诗都让这个艺术境界更加饱满。这是一个更悠长、更澄澈的诗境。
程千帆在作于1982年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末尾总结并且预见了这首诗会面对的审视:“每一理解的加深,每一误解的产生和消除,都能找出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认识,是无限的。今后,对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理解将远比我们现在更深。虽然也许还不免出现新的误解。”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