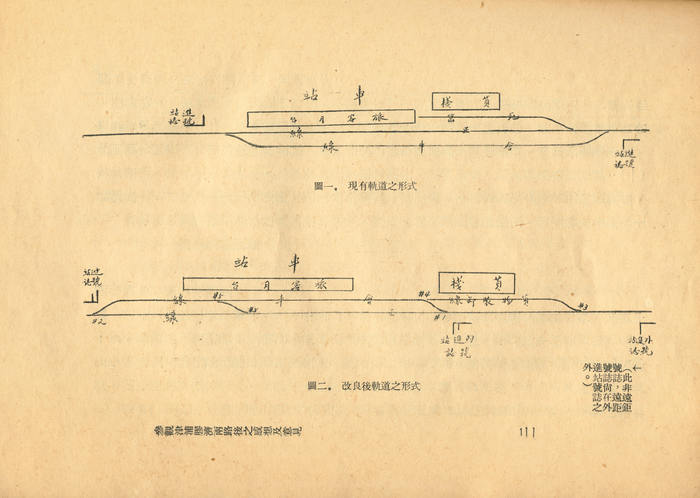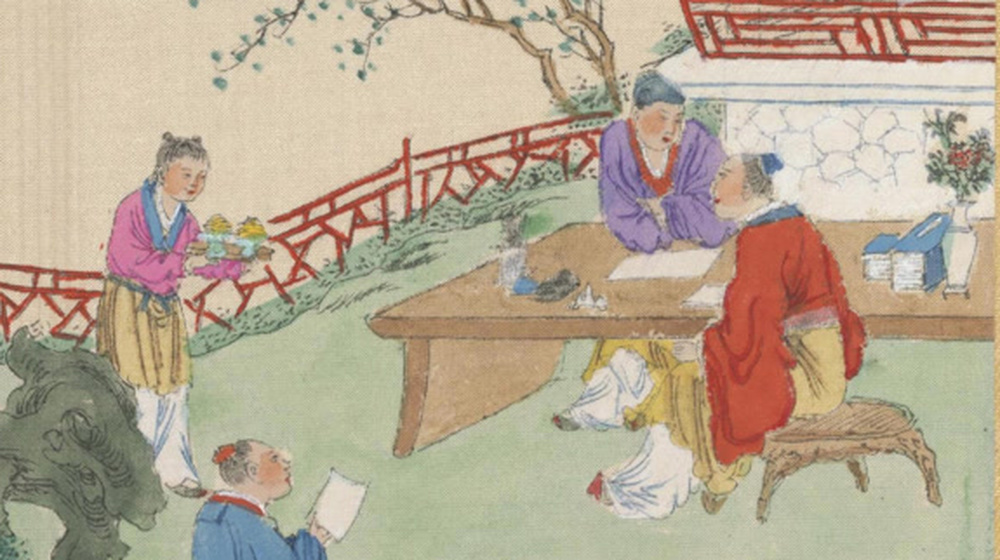新黄河记者:徐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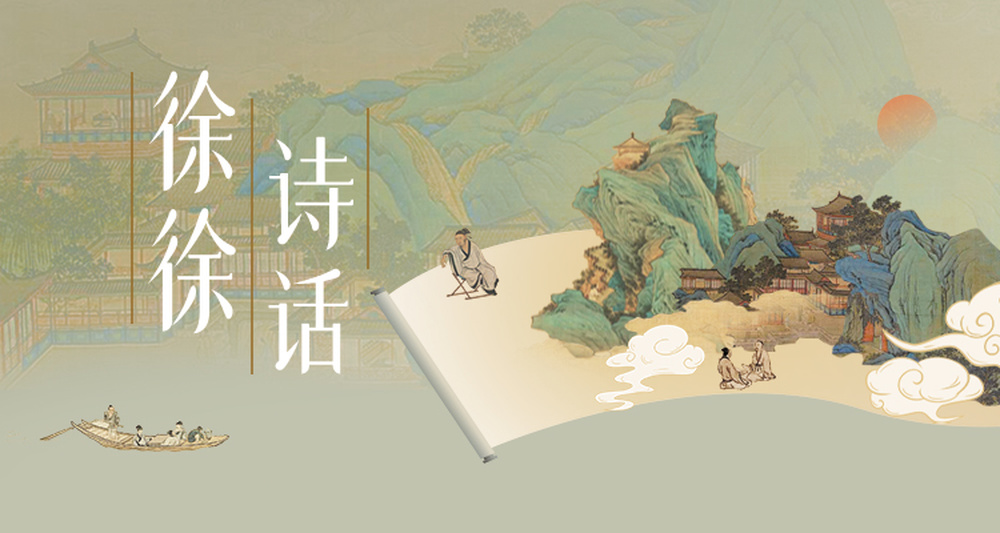
最初读韩愈,并不是从他的诗歌(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天街小雨润如酥”之外),而是从他的文章《祭十二郎文》开始的。韩愈如泣如诉、令人声泪俱下的文字之外,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能够坎坷至此”。
韩愈在文中简述自己的凄苦生平:
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
每一句话背后,都是一个人生命中入心入骨、雷霆万钧的伤痛。不只如此,韩愈后来又在中年痛失爱女。这样的伤痛,韩愈在生命中经历了一遍又一遍。奇迹的是,他并没有倒下,似乎这些痛苦和磨难都化作浇灌这个寥落生命的春雨,令这个生命反而更加茁壮和坚毅,最终成长为蓬勃浓郁的参天大树,此后再大的风雨也无法撼动他。他的心灵没有变得枯槁脆弱,而是愈加丰盈强大。韩愈就是那么挺拔、高傲和坚固地屹立在中唐文坛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他让我不敢靠近,只愿意远远地、虔诚地仰视。
不妨简单对比一下同时代诗人孟郊。孟郊一生也是坎坷而困顿,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屡试不第,晚年丧子。《唐才子传》中说孟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把两名诗人的生平放在一起对比并不是“比惨”,看坎坷人生给诗人带来了什么,而是可以更直观地意识到韩愈生命之热烈和坚韧。孟郊的诗歌底色交织着寒苦、孤寂与生命焦虑;而韩愈的诗歌则呈现出更多样的面貌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差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诗人本身的精神硬度不同。
我们都喜欢“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样的韩愈。这几首诗流传虽广,却并不是典型的韩愈。阅读诗歌,多数读者会喜欢那些轻盈昂扬、舒朗明媚的诗作,因为这类诗歌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读诗,原本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所以,初读能够代表韩愈典型诗歌理论的作品,我们大抵是不会喜欢的。文学史上把韩愈诗歌的最鲜明特色总结为“狠重奇险”,《石鼓歌》是这类风格诗作的代表: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石鼓歌》是一首很长的七言古诗,以上是这首诗的节选内容。直观看来,这首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好读。石鼓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十块鼓形刻石,上面镌刻着籀文(大篆)诗歌,记录先秦时期国君的游猎、祭祀等活动,是一种颇有史料价值的文物。当代考古学家认为石鼓是春秋时期秦国刻石,韩愈以及当时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文物。这些镌刻的文字称为“石鼓文”,韩愈作《石鼓歌》强调石鼓的珍贵,呼吁朝廷保护石鼓。
节选的这一段诗歌大意是,石鼓经历了千百年的日晒雨淋,多亏鬼神的保护才得以流传至今。你(指张生,即张籍)从何处拓印下来这没有丝毫错误的完整文本的?石鼓文文字庄严,义理精密,字体与隶书和蝌蚪文不同。年深日久,石鼓上的文字难免有缺失的笔画,就像是利剑斩断了蛟龙一样。后面四句,韩愈用奇特的想象来形容石鼓文的文字,然后叹息采风编诗者,甚至孔子没有把石鼓文收录进去,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且不说这首诗的题材是较少入诗的枯燥的“金石学”,单是语言文字就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阅读障碍。这自然与韩愈的诗学理论有关,他强调,“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说明诗人有意识地在遣词用句上避开流俗,寻找新奇的用语。这是一种自觉的创新意识,诗人试图开拓出一种前人尚未尝试过的语言风格。或者说,这是一种语言的冒险。
很大程度上来说,韩愈的这种冒险成功了。比如“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几句用来形容石鼓文的字体形态,韩愈大胆地将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本体和喻体联系在一起,确实带给读者一种新奇而又充满气势的阅读体验。“鸾翔凤翥”洋溢着袅袅仙气,“珊瑚碧树”是清新的自然景象,“金绳铁索”的气质生硬而充满力量感,“古鼎跃水”则既有古意也有动感。这些词句新鲜又形象地让读者了解到石鼓文的样貌。这种语言风格硬朗险怪,却又大开大合,一泻千里,狠重粗豪与畅快淋漓并存。在韩愈笔下,“狠重奇险”也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力量,这不是此前我们认识的常规意义上的诗歌之美,韩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诗歌美学。
韩愈有两句诗非常出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两句诗出自《调张籍》,后世多用来说明李白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实际上这首诗也是韩愈“奇险”风格的代表作,诗人这样来形容李杜的诗文风格: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
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
……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韩愈用这些宏大、少见而又奇险的意象来表达李杜诗文的风格和巨大影响,他用惊心动魄的语言写出了李杜诗歌是如何“惊心动魄”。清代学者宋宗元编撰的唐诗选评著作《网师园唐诗笺》中用八个字来评价“我愿生两翅”以下几句的诗风:思入淼茫,笔吐光怪。
尤其是“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两句,奇幻的想象力不输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等句,不过李白的句子更加浩渺浪漫,而韩愈则更奇崛险怪。韩愈也是有意识学习李杜的,因他追求“尚奇”的艺术风格,故而从前人诗歌中汲取的也多是其奇崛的部分并且加以发挥创新,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却又浑融而不见锤炼的痕迹。
对韩愈的这种诗歌特色,还是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评价更精准:韩吏部诗歌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